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近日,一部2024年上映的4集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下文简称《道格拉斯》)重回大众视野,登上豆瓣一周全球口碑剧集榜,并收获9.4分高分。“反杀渣男的高段位复仇”、“燃过《初步举证》”、“新闻界老登覆灭记”都是有关此剧的讨论词条,观众观剧时频频高呼“爽到了”。

在“复仇爽剧”的标签下,《道格拉斯》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职场性别歧视的严肃故事。故事开始于社交媒体上爆出知名男主持人道格拉斯于私人酒局开了一个性别歧视的玩笑,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玩笑究竟是什么。起初无人在意这则推文,直到道格拉斯的主持搭档麦德琳转发原帖佯做澄清,表示她相信道格拉斯的为人,帖子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麦德琳声称她这一行为是在向全社交平台不信任道格拉斯的人宣战。
针对道格拉斯的失德,麦德琳借用公众舆论的裁决,让道格拉斯最终被封杀。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得知麦德琳曾遭受上司托比的性骚扰,而道格拉斯知晓且默许了一切发生。《道格拉斯》全剧避开了对明确有性骚扰行为的托比的审判,将关注重心放在了道格拉斯这一“沉默的帮凶”之上,这也触及到了“取消文化”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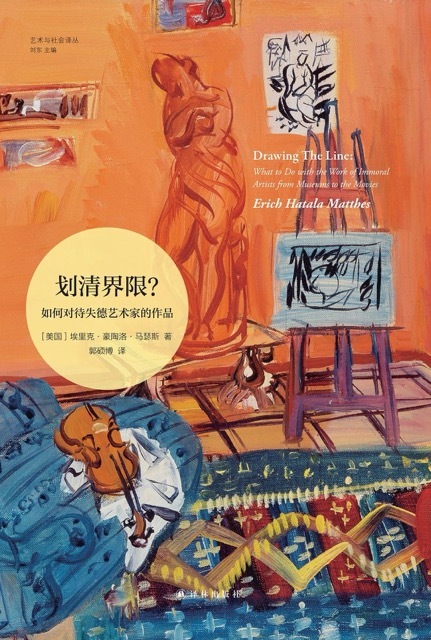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2024-8
在讨论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专著《划清界限》中,哲学家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区分了两种“取消”的情境——有的被取消者是明确犯下了暴力罪行,而另一些被取消者可能只是发表了一些争议性言论。后者是否该被取消、谁有权力对后者进行“取消”、对后者进行“取消”的合理限度在哪里,都是迄今没有确切答案但值得持续讨论的议题。
本文试图说明《道格拉斯》一剧并未直面上述问题,而是通过复仇爽剧叙事的逻辑悬置了对取消文化复杂性的讨论。麦德琳的复仇并未完全成功——当“取消”过于顺利地达成,惩罚裁定失去了充裕的协商空间,系统性的变革很难真正实现。
何罪之有?:“取消文化”及其争议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剧名中的“取消”一词来自“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一种社群抵制行为,即用举报某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认同的政治正确,发动舆论讨伐并力求将其封杀的活动。大众媒体时代以来“取消”事件层出不穷,从J.K.罗琳的“恐跨言论”使《哈利波特》遭到全面抵制,到杨笠因性别笑话遭受追击批评,“取消”成为了败坏一个人的公众声名、限制人的公共表达的强力手段。
在本剧中,首先让道格拉斯面临“取消”风险的是一则有关性别歧视的笑话。社交平台上有账号爆料,道格拉斯在侄女的婚礼上讲了一则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笑话来活跃气氛。剧中没有涉及笑话的具体内容,但因这个难经证实的事实本身,就调动了道格拉斯背后的许多力量进行危机预演。

道格拉斯面对这一推文带来的连锁反应愤怒不解,要求他人解释“我究竟何罪之有”。这一情节设置会让我们回想起此前同样讨论度颇高的舞台影像作品《初步举证》。在这两部作品中,女性都作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孤身进行“斗争”。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施暴者明确犯下性侵罪行,面临法律系统的审问;而《道格拉斯》中,性别歧视玩笑很难从法律层面定性。

西方文化界有关“取消文化”的争论也触及了相似的困惑。2020年7月7日《哈泼斯杂志》(Harper’s)发布了一封由众多不同政治派别文化人士的联名信。这封信写到,“不容忍反对意见,公开羞辱和排斥成风,倾向于将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德确定性中【……】教授因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而受到调查;研究人员因传播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被解雇;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有时仅仅因为一些笨拙的错误就被罢免”。在此,这些联名信的参与者表达了自身的担忧:有时候一个稍显轻率的玩笑或并非决定性的失误就可能导致一个人职业生命的终结。
目前关于上述议题存在两方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取消”是一种自主权的表达,正如作家奥斯卡·施瓦茨(Oscar Schwartz)所言,“虽然在取消文化中可能存在附带损害的情况,甚至有些被指控的人可以说是无辜的,但还存在更为紧迫的问题:我们本应信任的机构为何对少数群体面临的许多问题充耳不闻”,在此意义上,向上层精英发出反对的声音是让边缘人物的观点被看见的重要手段。
而反对者则认为“取消”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且会激发不宽容的社会氛围,让人们有组织地排斥任何观点相异者,这样一种风气甚至会吸引更多人加入非黑即白的阵营。
未完成的复仇:爽剧逻辑与幽灵般的笑话
在《道格拉斯》中,“取消文化”的诸多争议在悄然间被置换为个人复仇的大女主叙事,对于这出完美的报复,观众高呼“爽到了”,本质上是因为麦德琳的举动所完成的是一场大快人心的“私刑”。在《法律简史》一书中,法理学家桑本谦指出正义存在着一个生物学前提,即人人都有一种以牙还牙的道德直觉。麦德琳遭受的“伤害”,无法获得法律和公权的介入,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层面的成功复仇满足了观众的道德直觉,带给人们巨大的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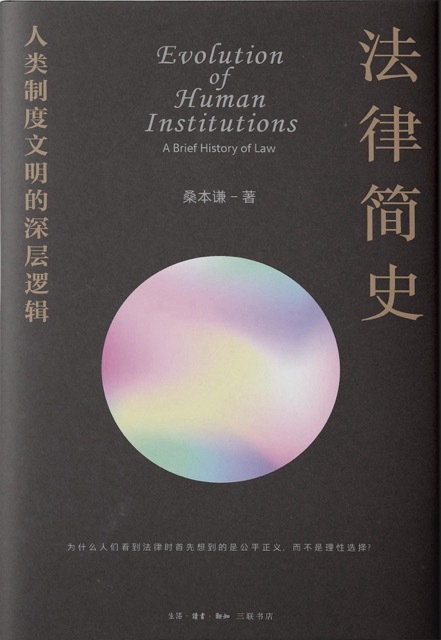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10
但在为麦德琳的成功复仇感到“爽”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编剧在情节细节处留下的暗影。麦德琳并非因为道格拉斯的玩笑才展开“复仇”,她的初始动机源于她遭受托比骚扰时道格拉斯未伸出援手的失望。在整部剧里,麦德琳从未将高涨的恨意指向侵犯者托比,却专注于惩罚道格拉斯这个旁观者。在此,“复仇”仅仅来自于麦德琳受到冒犯和未获得支持的主观不满,有关“复仇”真正的对象以及“复仇”行为本身合理性的讨论都被悬置了。
如此,麦德琳的胜利更多是凭借对现有系统逻辑的遵行(如利用自己身为女性的性别资源操纵道格拉斯)设计的一出精妙复仇,而非对系统本身造成撼动。麦德琳对此有清晰的觉知,在剧集的最后,麦德琳参加一档电视节目,主持人称这一事件“是全体女性的胜利”,麦德琳则坚称,这只是一场属于个人的胜利。

在这样的爽剧叙事逻辑之下,尽管《道格拉斯》一剧并未对“取消”的正当性问题作出直接回应,却在制造“爽点”的同时于隐微处透露了对“取消”的警惕与反思。在《道格拉斯》中,麦德琳以大众舆论为手段,让道德责备(blame)直接上升为了惩罚裁定(punishment),即对于道格拉斯失德行为的批判成功毁灭了道格拉斯的职业生涯。
道德哲学中有关道德责备与惩罚裁定的讨论认为,道德责备的功能是修复和继续关系,避免被批评者的再度违规;而惩罚行为会强制施加无法收回的代价给违规者,倾向于终止交流而非恢复交流、破坏关系而非修复关系。从这一角度理解,“取消”正是一个明确的惩罚行为,“取消”本身意味着要么存在,要么全然封杀,其间没有中立地带,不同的话语立场之间没有协商的空间。
惩罚的效力越是彻底,越是要求程序上的清晰,然而马瑟斯提请我们注意,“取消”的过程似乎总是发生得过于迅速和随意,公众作为一个群体在进行问责时很难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标准,最后极易变得仅凭个人喜好与偏见作出判断。正如播客“展开讲讲编辑部”所提及的,麦德琳“借刀杀人”最终依赖的是新的一重置换:起初性别歧视笑话事件久久未对道格拉斯造成直接影响,直到将性别歧视的言论置换为对体制(新闻业)和阶级的冒犯,道格拉斯才成功被“取消”。此时“取消”的成功与否不再关乎“正误”的讨论,而只关乎党同伐异的不同群体之间谁的声量更响。

当“取消”成为了一出过于顺利的爽剧,我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在《道格拉斯》的整个爽剧逻辑中,那个幽灵般的笑话数度被道格拉斯的支持者尝试赋予真身,他们致力于创造一则“厌女又不那么厌女的笑话”,以承认事实的同时维护道格拉斯的声誉。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究竟怎样的笑话让女性感到冒犯,而又不至于过于冒犯,只能由女性的主观经验裁定,而无法由男性旁观者来想象。

《初步举证》亦揭示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有一些受到伤害的私人化体验永远无法清晰呈现为法律证词,甚至无法被证实或证伪,只能在反复的对话与言说中渐渐浮显出其轮廓。弱势群体的这一部分主观性体验如何被客观的制度体系所承认、维护,是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但是伴随着麦德琳进展迅速的复仇,想象和讨论这则笑话以及女性的受冒犯经验变得不再必要,阶级冒犯作为一种清晰的事实取代了性别冒犯的模糊性。通过这样的结局设置,《道格拉斯》暗示,“取消”让对话的空间被迅速略去。当“取消”的结果达成,没有人再关心声量更小的群体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格拉斯》本质上是一出被“爽剧”外衣包装的恐怖故事。
参考资料:
[1]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划清界限》,郭硕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4年。
[2]桑本谦:《法律简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3]展开讲讲编辑部:“春天广播电视报:人生没有重启,只有一镜到底”https://mp.weixin.qq.com/s/udBusBAyQmbwDyIYaUFTiA
[4]“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5]“Cancel Culture: Is Cancel Culture Good for Society?”
https://www.britannica.com/procon/cancel-culture-debate
[6]Malle, Bertram F. “Blame and Punishment: Two Distinct Mechanisms for Regulating Moral Behavior.” [In] B. F. Malle & P. Robbins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7]毛馨儿X张杨思颉X王斐然|《初步举证》:那些无法言说创伤的女人们, 构成了三分之一,远读公众号,2025-03-23。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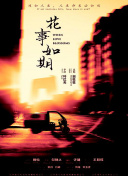
 48158
48158 46
46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 4
4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 78
78


 63524
63524 2
2


 62738
62738 4
4


 31856
31856 47
47


 71272
71272 50
50


 83067
83067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94331
94331 53
53


 29063
29063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 44
44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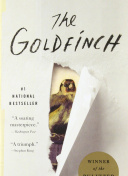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


 1
1


 63428
63428 58
58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46245
46245 22
22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 35
35

 45060
45060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42
42


 41857
41857 2
2


 66369
66369 8
8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