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辉夜姬:白鹿原220分钟完整版-从绿绒蒿到植物远征计划:植物学知识的生产与权力(下)
【编者按】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云南,一场关于植物、科学与文化的复杂互动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从早期西方植物猎人的探险,到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实践,植物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始终与殖民扩张、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性进程密不可分。DBN(Decolonial Being Network)于2月16日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举行题为《从绿绒蒿到“植物远征计划”:滇藏植物知识与多元解殖探索》的线上对话,聚焦于三个核心议题:滇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知识如何被纳入现代植物科学体系,植物园作为知识生产场域如何塑造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当代艺术工作者如何重新审视和呈现这段历史。王沁雪的研究《绿绒蒿属:蓝罂粟及其现代植物学知识与佛教认识论》追溯了绿绒蒿来到邱园的前世今生。策展人戴西云和艺术家程新皓通过解读植物猎人的游记、考察日志和科学实践,揭示了不同认知体系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与文化转译。澎湃新闻摘发部分对话内容,经对话人审定。本文是下篇“植物猎人、中介者与民族国家”。
程新皓:当沁雪在讲的时候,我自己也被带回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场域,不管是全缘叶绿绒蒿之于E.H.威尔逊,还是蓝花绿绒蒿之于金顿·沃德,其实这一片横断山区的山地,也算是我非常熟悉、被认作故乡的一片土地,而这一些从19世纪末就不断进入到这片地域的植物猎人,其实在当时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外部的视角。从此在本地人看来,这个世界的知识就不再只是一种自己熟悉的、在身边的本土知识,而是有了一种更加遥远的、难以理解的、难以进入的、我们今天够称之为“世界知识”或者“帝国知识”的这样的一种外部。
这种外部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我们来谈论的内部,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的转换。这样的视角切换是如何完成的,它又是在什么时间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的,这是我和西云要做这样的一次远征的核心之一。
在这些知识还没有成为我们今天最熟悉的、可以视而不见的透明知识之前,这群植物猎人是怎么样来到这里,怎么样在他们的知识和世界之间,和此时此地的知识、人和物种在进行着交流沟通,建立起某种联系,最后实现了这样的知识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转变?
虽然我接下来讲述的可能是这个例子或那个例子,但这些例子之间其实是有着不可忽略的暗线的勾连。
就像沁雪的分享当中提到的,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后,规定了英国人进入中国时有着哪些权利,有着怎样的优待政策。为什么会有《烟台条约》?在1875年发生了著名的马嘉理事件。而《烟台条约》的出台就开启了之后英国植物猎人大量进入中国西部和西南土地进行植物采掘的滥觞。时间往后推移三十年,在1904年有一位苏格兰的植物猎人叫福瑞斯特(George Forrest,中文名叫傅礼士)也同样来到了云南。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凑巧。1905年,在他开始第一次植物远征时,走到了澜沧江峡谷当中。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也知道,1905年在澜沧江峡谷里面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叫维西教案。当时藏区的人民在反抗远道而来的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背后的这一套新的权力关系,他们用的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把教堂全部烧掉,把外国人全部杀掉,把信教的人杀死。
刚好在此刻傅礼士来到了这里,于是他进入云南经历的第一个事件,就是他侥幸逃出。和他在一块儿的其他所有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杀死了。但这没有使傅礼士失去信心,在此之后的28年间,他一共七次在云南进行了他的植物学远征,采集了上万种标本,以及数千种植物的种子或者活体,把这些植物的标本、种子活体以及伴随着的所有知识送回到了他的大本营——英国北部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时傅礼士引种回去的杜鹃、采集回去的标本和那些他手书的标本上的标签。
但是当我们进行如此叙述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叙述。因为当我们回到具体历史场景时,一个来自苏格兰的植物猎人,他怎么能够进入云南和进行这样的本地操作呢?在他和云南的土地之间,在他与云南的土地和那些有待发现的本土物种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中介。这些中介在哪里?他们如何发生作用?实际上最直接的中介就是他的助手,他雇佣来帮助他进行远征和采集的本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群人来自丽江坝区一个叫做雪嵩村的纳西族村子里面赵姓的一系列亲族,其中可能最有名的是他的主要助手赵成章。在他的叙事当中,赵成章的名字是“老赵”,而七次植物远征其实更多是由赵成章带领着其他助手来完成的,傅礼士只是名义上的领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加有趣的知识和视野之间的转换(shift)。在这里转变的并不是一种黑暗的、有待发现的、未经命名的植物学对象进入到帝国知识的视野当中,最后被照亮的过程。而是一群本身就有着对这里丰富经验的本地人,在他们自己的知识支持系统里面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东西,而他们如何把他们熟悉的这些东西转变为另外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是无法把握的帝国知识里面的一种合理对象,这就是这些纳西族助手在完成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有些时候充满了戏剧性。比如说在1931年的时候,傅礼士生命的倒数第二年,他最后发现了一种巨大无比的杜鹃,他最后命名为大树杜鹃(Rhododendron protistum var. giganteum),用的是giant的拉丁文词根,就是巨大的杜鹃。它实际上是在腾冲附近的高黎贡山界头镇附近发现的一种巨大的杜鹃。他认为当时西方的学界不会相信他所描述的这样的巨型杜鹃,所以他在发现了杜鹃之后,找到了他的助手,让他们把株直径(不是周长)超过2.5米的杜鹃给直接伐倒,把它最大的一截枝干运回到了英国,现在还保留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当中。他在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说他通过中介最后完成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不简单是一种对象的发现命名,而在这里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也许我们在这些事件当中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它能够折射出来的那些关系、那些权力的关系,是比“在知识之间”的这样轻飘飘的描述要多得多的。
再之后的一年1932年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傅礼士他在腾冲决定出门散散心去狩猎,他带着他使用了多年的猎枪来到了高黎贡山。他看到了有一只鸟停在了一棵树的上方,于是他进行了瞄准,扣动了扳机。在扣动扳机之后,鸟儿显然没有被击中,振翅飞走。而在这一刻傅礼士倒下了,这一声枪响促成了他的心脏病,他最后就死在了他在这里工作了28年的云南土地上。
这个故事并不因傅礼士的生命终结而终结。我们今天再去看傅礼士那些运回苏格兰、运回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档案时,我们会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档案当中,在那些植物学的标本当中,是傅礼士用钢笔用英语手书的关于采集的信息,而采集人就是傅礼士本人。而只有最后一批标本,也就是说在傅礼士意外死亡时还没有来得及替换标签和运回英国的那批标本当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记载。我们发现那批标本的标签上写的不是用钢笔书写的,也不是英文,而是他的助手老赵(赵成章)用毛笔书写的汉字。
也就是说,只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在和云南的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的中介。然而在这些事件,在这些所有的整体性的知识和对象转变为帝国知识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中介的部分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似乎变得它需要被透明,需要被丢弃,从而使得这些东西能够被纯化为、能够被蒸馏为某种合理的帝国知识的一部分。在这里在傅礼士的事件当中,似乎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在今天我们回到洛克故居周围,我们还能看到的是并不以旅游目的地存在的傅礼士的故居,实际上就是赵成章家的主宅。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赵成章的后人,以及在这个村子旁边的雪山坡地上,甚至在赵家的墓地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墓。当擦去墓碑上的浮尘和青苔之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赵成章本人,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死在了雪松村,而葬在了赵家人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上。
这里还有另外一位植物猎人,也是刚才两位隐约提到的约瑟夫·洛克。他同样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傅礼士有所交集。在1922年的时候他来到了这里,是傅礼士帮他联系的当地人租的房子。然而他们两人互相看不对眼:一个古板的、不在乎当地文化和知识、认为这里只是一种落后的、只是一种有待发现的知识对象的英国绅士,和这样一位其实连自己的学历都是伪造的、奥地利裔的美国植物学家——这样一个在骗子和学者之间身份有着微妙浮动的人,他们怎么会互相看得对眼?
但是无论如何,从1922年这个时间点开始,约瑟夫·洛克就开始了他在云南作为植物猎人的工作。当然最后约瑟夫·洛克滑向了另外的一级,他发现当他在这里进一步深入的时候,这里的文化并不是那些可以被斥之为野蛮、从而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可以从标签上摘除的那样的东西。而是他发现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不再是文化之后的对象,而是覆盖在对象之上的本地文化。以至于在1950年他最后不得已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他真正带走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他把它翻译成了英语的东巴文。
当然我们今天说东巴文,它不是一种日常语言,它是一种在仪式当中使用的象形文字的一种对象。然而洛克的兴趣正在于此,正在于这些几乎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不可理解的文字和这些文字当中承载的那些让他着迷的这个地方的文化。
这样的一些关系就是我们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再详细展开,但是在洛克早期的在云南和四川的考察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他非常在乎的就是什么东西可以通过中介获得,什么东西可以在中介的过程当中被他创造性地把握到。
而这些中介也许有些时候是一些出其不意的对象,就像这两张照片,其实是他应该是在川西木里一带的藏区所拍摄的当地喇嘛的照片。在这个照片当中,让我们关注到的点是什么?你会发现是照片中间突兀存在于此的留声机。为什么会有一台留声机普遍存在于洛克当时拍摄的各种照片当中?


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摄影术并不被当地的文化所直接接纳和认可,而是它有可能被视为某种带有危险性的妖术。这些人对于摄影怀着某种天然的抗拒,或者说至少不是顺滑的接受。但是洛克发现他带去的另外一样技术物却完全受到了欢迎,就是留声机。
他带着留声机,带着当时最著名的欧美男高音卡鲁索的唱片。他发现他在播放卡鲁索的歌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着迷了,都围到了唱片机的边上。于是他找到了一条可能只有他才能够想到的拍摄照片的方法,就是他首先支架起来的不是三脚架和庞大的摄影设备,而是唱片机,而是卡鲁索的歌声。当人群聚集、人群围拢的时候,他在有条不紊地架上他的相机,吆喝一嗓子,大家把目光投向他,于是这些照片就在这里获得。
在这里你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在遥远的知识、遥远的帝国和在此时此地的植物猎人,或者说这些最后转变为某种文化中介的植物猎人,与当地之间的某种轴线和关系。在这里它并不是一种两极化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二元化的东西。这些看似二元的系统当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发生中介的人以及这些建立关系的那些标志性的事件在哪里?它如何被重新揭示出来?这可能是我一开始进入植物猎人这个题当中,我首先会问出来的问题,也是当时我在做的作品所回应的东西。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到知识的另外一端的田野,比如说在今天的苏格兰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植物猎人曾经采集的、在100多年前种下的这些杜鹃花本身。以及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本土知识,在另外一种语境之下在这里重新变得重要了,重新变得它不能够再透明,而是你必须去标识出那一些东巴文的符号,标识出中文的陈述介绍,此时此地,你在这些英伦三岛的物种和遥远的采集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完成的这样的知识和物的漂流和转移?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最早的傅礼士引种的杜鹃,以及刚才沁雪提到的金顿·沃德引种的以佛瑞斯特来命名的另外一种紫背杜鹃。当时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当中,我看了三天,一株一株地去寻找那些在植物猎人的记载当中出现过的这些植物,而由此就做了一个作品《复盗》。

程新皓,《复盗》 (Re-stole, 2019, 2024),装置与档案(杜鹃枝条,玻璃罩,图片,档案),展呈照片,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我找到的最早的一株杜鹃在1914年,实际上就是福瑞斯特的第二次远征当中,在丽江采集的叫亮叶杜鹃的这样一种杜鹃,它在100年前被种植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而在今天它依然存在于那里。我发现它的一枝枝条其实已经是被风吹折,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于是我就趁人不备,悄悄地拿出一把园艺剪,把枝条给剪了下来,重新把这株杜鹃带回了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中国的云南省,并且把它和那些我拍到的以及和这个故事本身的那些背景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刚才西云提到的在她的展览当中出现的这件作品。

程新皓,《复盗》 (Re-stole, 2019, 2024),装置与档案(杜鹃枝条,玻璃罩,图片,档案),展呈照片,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另外一件平行的作品是叫musica proibita,其实就是我在云南的山边找到了一株正在盛放的马缨杜鹃,我背了一个黑胶唱片机,带了一张卡鲁索的唱片,最后在云南的咆哮的狂风当中,为这株杜鹃播放了一曲卡鲁索在唱的歌声。而那首歌的内容是一位男性正在追求他的梦中的对象,然而这是一种求而不得的那种爱的压抑,是一种禁忌的爱,最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录像作品。
讲到这里似乎好像很多关系都在这里面阐明了,然而在和西云的交流和沟通当中,我发现仍然有很多的东西在上述的这些叙事当中被忽略了,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也许才是真正需要被重新提出和重新面对的对象。
比如说在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个知识之间的中介,无论中介到底有多少层,最后屹立于两端的还是遥远的帝国知识,或者说遥远的欧洲或者美国为代表的一端,和在彼时彼刻,或者说此时此刻我在面对着的我的故乡,这些知识发生的这些物种所在的地方,云南。似乎还是这样一种外来的知识和本土的知识,外来的文化和本土的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不管你加进去多少新的行动者,似乎轴线能画到它的两端,就是这样的两个东西。
真的是如此吗?是否有可能去引入新的变量,有什么真正重要的变量是在这样的叙事当中被忽略的?我们在这里可能再花一点时间讲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来看在这里新添加进去的东西是什么?
西云提到了陈谋和吴中伦在1934年进行的那一次环绕了整个云南边区的植物远征。为什么是1934年?我们如果把时间稍微往前推移一点,在1934年初,这里发生了“班洪抗英事件”,其实就是在云南的西部边陲,当时已经占据了整个上缅甸的英国殖民者,试图去蚕食那些在当时还晦暗不明的灰色的土地。
当他们迈得最远的时候,就有一队英国的殖民者,到了当时佤族人控制的班洪、班老的这样一片区域,最后受到了当地人的迎头痛击。而这个事件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以至于在云南当地最后组建了义勇军去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以及在更遥远的可能不是前线的地方组织起来了对前线的募捐,组织起来了一种广泛的声援,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去重视这件事情。
1934年,当时的中央政府研究之后,决定要派出一个边界考察团,最后发现只有一个人愿意去:一位云南籍的叫做周光倬的地理学者,那么就由他组成了边界调查的核心骨干,其实就是他和当地人,在当地人的辅助之下,到这些发生了边境事件的地方调查它的来龙去脉,去调查这个地方的地理和政治的归属的沿革。接着,当时的科学界也想趁这个机会去那个地方走走,因为这不是一个随便能去的地方,哪怕到了50年代在云南西部边界,仍然不是一个那么安全的能够随意抵达的这个地方。于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农学部的植物学家陈谋先生和当时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学生——20岁出头的吴中伦先生,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考察植物远征的考察团,他们和周光倬一前一后来到了云南的西部,最后沿着西部的边区进行了一系列对象不同的考察。当然在1935年的时候加入的还有那些民族学的考察,我们熟悉的像方国瑜先生的《西南边区考察记》,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的。这里,我们会意识到一个事情,即这里生发出的所有的知识,它不是一种中性的知识,不是一种可以简单被抽象为“知识”的这样一种中性对象,而是有着一个知识范畴之外的更大的背景。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殖民与反抗之间的冲突,具体化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主权的归属。曾经中性的知识在这里,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再中性。
从1934年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植物学家来到了云南,站在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对那里进行了考察、命名、归档,使得这些知识的归属权不再需要跨越重洋去邱园当中寻找,而是在中国土地上、自己的机构当中,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伴生于民族国家的科学知识。
讲到这里,似乎有一个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使用知识去抵抗那种文化和实际的殖民侵略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我们重新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它真的是像我们刚才的讲述当中的那样一种本土知识和帝国知识之间的这样的对抗吗?你会发现,不是的。这里使用的、形成了一种真正有效的对抗的武器的知识,恰好是来自西方的知识本身,恰好在这样的冲突和对抗当中,这种知识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权力和知识。而在这里,那些本土知识便以一种被双重遮蔽的方式,湮没在了历史当中。
在这里,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对象,或者说出现了一根新的轴线: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他者和本土之间的关系。有一系列新的关系出现了:他国和本国的关系;可以被他国所有也可以被本国所有的世界知识和那些在一种对抗的姿态当中重新被遮蔽的本地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些一系列的新的关系就在这里建立起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个层面。
而第二个层面是什么?这些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能够直接以一种降临的方式获得的,它依赖的是一个行动的肉身。这些植物它所在的地方,它最终会有一个跋涉千里的人,以某种必然或者偶然的方式,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到达特定的地方,最后一切变得可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具身的行动者,他是如何行动的?在这里最后促成了所有事件以及最后促成了所有知识,成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模样中间的那些必然和偶然是如何发生的,那些事件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勾连在一起的?具身性和行动,这也许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二个轴线。
讨论部分
王沁雪: 刚才特别有共鸣的一点是,知识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的扩张不仅仅是科学帝国、技术的扩张。如果单纯是技术的扩张也就罢了,但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整体侵略。中国作为当年权力结构中比较被动的一方,在所谓的超英赶美的实践中,把自己的本地知识西方化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或者亚洲面临的,而是整个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使得现在的文化变成了只有一种文化下面的所谓的多元,但并不是每一个多元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它会变成一种认识论上的单调。
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论上的丰富或者多元?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正确问题,而是揭示出了整个现代性的一个大问题:单向度的思维。这体现在不断单向度的知识积累或者速度的增加上,比如火车追求速度,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摩天大楼追求高度,知识追求的是一种量的积累。现代化的过程即通过殖民过程,将这种单一的认识论的思维和情感形式普遍化,这一过程得益于航海和军事技术的推动,使这种断裂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重要的似乎不是知识量的增加,而是知识性质的改变。知识的量越多,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反而越窄了。因此这种单向度本身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
所以我们无比需要非现代(non-modern)的认识论。但就像哲学家Yuk Hui说的,“……非现代并非为尚未存在、将来会变成现代的东西,而是作为那些抵抗变成现代的东西,并且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代的东西。”
另一点我想说我们需要将作为植物猎人身份的这些植物学家和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植物学家区分开。
首先是作为职业身份的植物猎人,这个身份是在帝国植物学系统下,为植物园、苗圃、商业植物园工作的一个职业角色。但是从他们的日记和私人笔记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很鲜活,他们认真对待职业,热爱家人。比如威尔逊第四次进入中国时,即使腿摔断了也要继续工作,他对待当地人很友善,愿意去尊重当地的采集者,与他们建立深厚情谊。但这些在大系统下的人性的闪光点往往不会被记录在正式的历史叙述中,也不会被记录在官僚化的植物学档案中。现代植物学系统把人变成了一个非人化的、纯职业性的植物猎人身份。
蔡昕媛:我们站在当下的时空位置,如何可能与不同知识背景的群体展开真正有效的对话?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那些将科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客观真理的群体时——无论是植物学界的专家,还是更广义上的公众——我们应以何种语言和姿态,去质询、交流,甚至共建多重认识论之间的桥梁?
戴西云:我先抛砖引玉吧。刚才沁雪提到植物猎人在个人视角下写的考察日记里,呈现出了他们很鲜活的个人形象。如果往前追溯的话,在这些专业的植物猎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大一批植物猎人,他们的背景并不是植物学。他们中有的是船长,有的是传教士,还有的是探险家,很多都不具备植物学的专业背景,也不是像邱园这种正规机构委任去做这项工作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是因为在大航海时期,随着植物学的建立,植物逐渐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众性的爱好,形成了“植物热”。比如说,“泡沫经济”这个术语就是从郁金香的倒卖中演变出来的。再比如,为什么这些植物猎人都蜂拥去云南,其实也是因为那里杜鹃品种的丰富性,除了新物种的命名,还有它们在经济上的价值。
在植物学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也逐渐参与进来,部分原因是这成为了一种花园爱好。当时如果你采摘到了奇珍异花,可以献给女王,王室和贵族也喜欢把这些奇珍异花作为佩戴装饰。比如土豆在早期引入英国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是可以食用的,但因为它的花很好看,所以被用作装饰性的佩戴物。
此外,植物科学画的热潮和广东沿海博物画的蓬勃,其实也都与植物热和博物热有着很大的关联。
所以,植物学和植物,早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就已经与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程新皓: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在实际经验中,我看到的并不是科学如何把其他认识论或狭义的知识系统覆盖,变成唯一的客观正确答案。相反,人们会很自然地灵活切换各种认识论和视角。当讨论科学时,他们可能会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当场景变为日常讨论,比如星座、占星术、命理之类时,科学的认识论就自然而然被悬置了,而且这里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灵活性是人类实践中自然具有的。
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些不同的认识论和系统当中,什么是可以跨系统讨论的部分?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系统和认识论放在一起讨论,同时又保持其有效性?
在每种不同的认识论中(不只是科学认识论),我们都可以去溯源,回到这些认识论最初提出时的真实事件中,寻找它真正的背景是什么,那些被我们忽略掉但作为前提存在的背景和偶然性是什么。比如林奈的双名法,虽然现在被广泛使用,但我们要问:物种真的可以用如此清晰的方式来定义吗?如果回到与林奈同时期的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那里,在物种的概念上会发现一种更加宽泛且一针见血的观点。
在非科学的认识论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那些被科学遮蔽的偏见,或者说科学本身带有的偏见,在其他认识论中只是以不同形式出现。
以云南腾冲的造纸植物为例:那里有两种用于造纸的植物,一种叫颠茄香,一种是小瑞香,当地都称为“构皮纸”。之所以用“构”来命名,是因为在汉人居住地区,构树是最常用的造纸植物。然而,构树属于桑科构属,而滇结香和小瑞香属于瑞香科瑞香属,从现代植物分类学来看,它们完全不是同一类植物。但在造纸这个功能性的角度上,它们获得了相同的命名。这可能反映出汉族人带着功能性思维,用他们熟悉的体系去重新认识和命名本土物种。
这个例子说明,科学认识论中存在的遮蔽问题,在其他知识体系中同样存在。这确实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复杂的问题。
蔡昕媛:20世纪的云南游记文本,除了透过植物的解读,还有其他哪些可能性?
程新皓:我直接说几部特别有意思的云南游记。当然我不把时间限制在20世纪,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以看到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诉求下是如何进入这片土地的,他们关注什么、记下了什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这些东西。
最早的是1866-1868年间的一支法国探险队,他们从越南开始想要顺着湄公河一路走到云南。这支探险队带有很强的殖民政治目的,他们想寻找一条进入云南的水路通道。他们一开始设想能否沿着澜沧江走到云南,或者说澜沧江是否能够成为这条水路。最后发现澜沧江不行,真正最合适的水路是红河,这也决定了后来法国对越南殖民政策的一系列倾向。
这支探险队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带了一位画家路易·德拉波特,他留下了最早的西方人关于云南的影像,而且是以写实的方式留下了数十张后来被印成铜版画的影像。这些影像在今天仍然可见,是关于云南最早的来自外来目光的记录。他们留下的日记是由当时的副领队(后来因领队死亡而成为领队)弗朗西斯·安邺(Marie Joseph François Garnier)所写,这份报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安邺报告》。
第二个文本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被杀的马嘉理的日记。他在从中国内地去中缅边境接英国探险队的路上一直在写日记,直到被杀前夕。他的日记留下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包括他在实验该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他发现如果以他认为的礼貌方式反而会被当地人欺负,相反如果学着中国官老爷摆出某种架子时,对方会自然地呈现出一些举动。他一路都在记录这样的跨文化细节。当我们阅读他的日记时,我们知道日记的结局,但我们也知道,他并不知道这一层关系让文本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刚才西云提到的那本书与这些日记是同一个书系的。作者沿着滇越铁路来到昆明,然后雇佣马帮沿着曾经的中缅之间的南方丝绸之路一路走到了缅甸的巴莫。有趣的是,在他出昆明城时,与他结伴同行的就是约瑟夫·洛克,这样不同人的轨迹就以这种方式串在了一起。
我们此行参考了很多资料,包括吴中伦和陈谋的植物采集日记,以及周光倬的边界考察日记。他们是前后相差一天后在中途汇合,一起完成了后半段行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了几乎相同的经历,这两本日记之间有很好的互相呼应作用。
说到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中涉及植物的只有陈谋和吴中伦的植物采集日记。更多的云南游记是每个人带着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怀着不同知识背景来到这里,并与这片土地发生了真实的遭遇。我觉得这些细节里折射出了很多从理论层面难以分析的东西。














































![触糖1V1骨科 我是杠精[快穿]](https://image11.m1905.cn/mdb/uploadfile/2022/0829/thumb_1_128_176_20220829011005853289.jpg)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 26
26


 48158
48158 46
46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 4
4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 78
78


 63524
63524 2
2


 62738
62738 4
4


 31856
31856 47
47


 71272
71272 50
50


 83067
83067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94331
94331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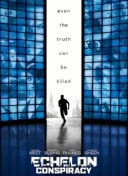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


 68942
68942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 44
44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89028
89028 4
4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


 62398
62398 1
1


 63428
63428


 63473
63473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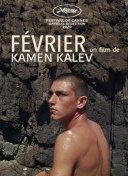 46245
46245 22
22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 35
35


 45060
45060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42
42


 41857
41857 2
2

 8
8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