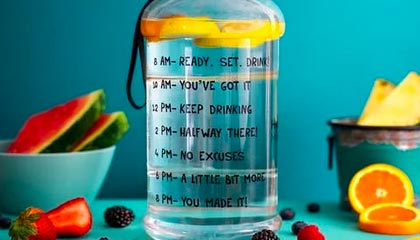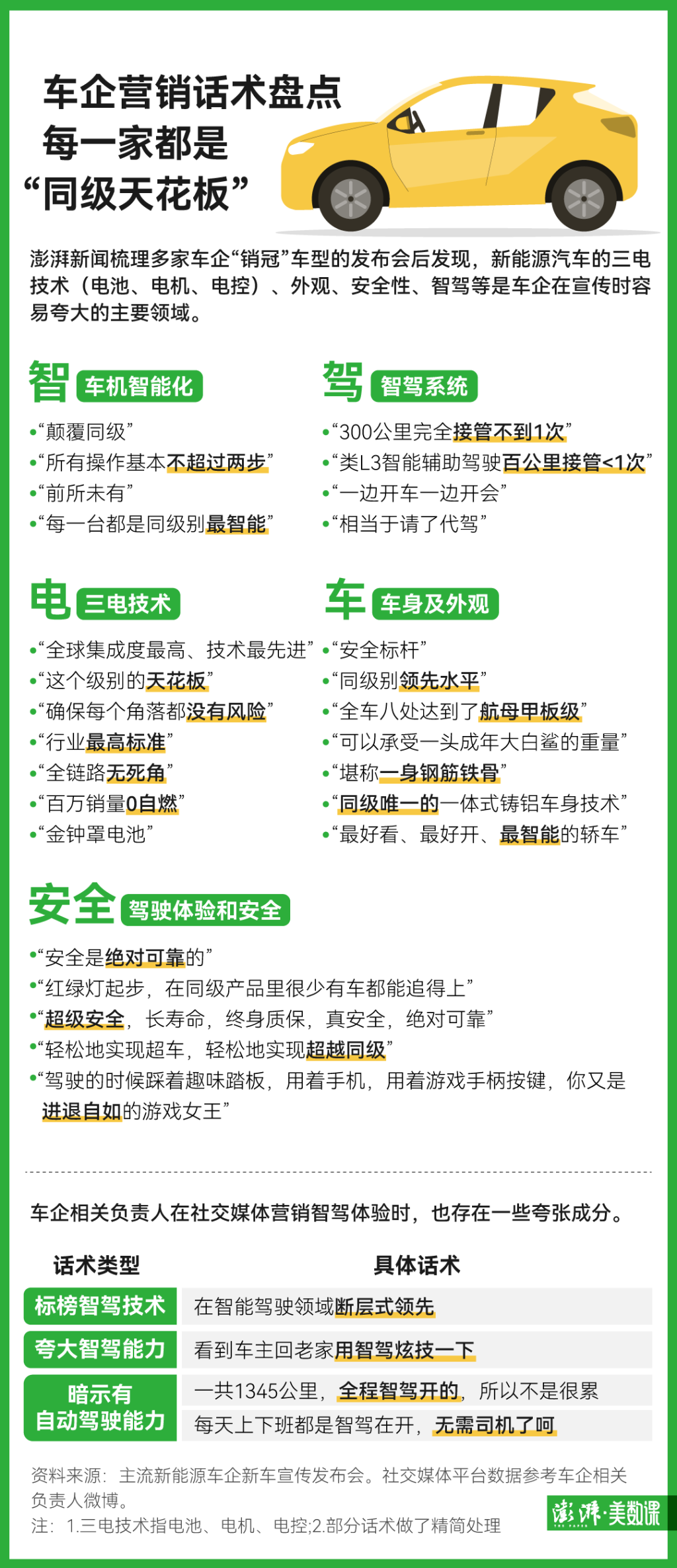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4年,脱口秀影响力愈发显著,已然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宣泄压力、探讨社会议题的重要媒介。那些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再次进入观众视野,他们用幽默消解刻板,将调侃解构荒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的关切。
不仅限于电视节目的舞台,脱口秀的触角早已深入社交平台与短视频领域。在这些更为碎片化的媒介中,段子成为新的传播载体,与文学、音乐、影视的跨界结合,也赋予了这一形式更新的表达维度。这一曾在小众地下文化中生长的艺术,如今跻身主流,成为解读当代生活的文化符号。它承继幽默的传统,也以自身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社会的集体焦虑。
“幽默”一词最早由林语堂翻译自英文“humor”,他通过创办《论语》半月刊,试图唤醒中国人对幽默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意识。正如杨笠所言:“语言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 如今我们希望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寻找到这种新语言形式的力量。
鉴于此,界面文化策划了系列报道——进击的脱口秀演员,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三篇:《刘旸教主:努力的速度要比岁数消耗的更快才行》。

第一次见刘旸时,他正在天桥艺术中心排练话剧《戏悟》,那天的北京刮着六级的大风,剧场外是狂风乱作,剧场内却有着温馨与笑声。刘旸头戴一顶黑色毛线帽,身着一件胸前印有一只举着花的小熊的毛线背心,被来探班的一位朋友戏称是他的“万年毛衫”。关于这件衣服,刘旸对界面文化如此解释,这可能是他内心的一个怪癖,有时会很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很幼稚可爱的东西。而帽子,则带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这一天的刘旸非常活跃,在排完一段煽情的戏份之后,他会不自觉地即兴发挥,现场加梗让场子热起来,以尽快消解掉剧中略显痛苦的氛围。排练间隙,他跟导演松天硕对一个站位的准确度意见相左,两人还为此打赌并下注,结果刘旸赢了,他无情地嘲弄起松天硕,还学起了《八十一难》(其在《喜人奇妙夜》中的作品)里的猴子,上演了一出“猴王易主”。
随时随地把舞台切换到爆笑模式,是喜剧人的职业属性之一。在早期脱口秀舞台上,刘旸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冷场,对现场人物情绪的感知异常敏锐,他可以在舞台上用夸张的表演让观众捧腹大笑,但也会在观众沉默时情绪跌入谷底。这种双重情感性,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将时光快速推进,我们会直接看到一个走红之后的刘旸。除了脱口秀、Sketch、话剧,刘旸还涉足书籍和播客,甚至成为了2025年B站跨年晚会的主持人,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很难用一个标签来定义他,也很难用一个赛道框住他。

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日子里,刘旸从不掩饰自己对成功的渴求,同时也会将内心深处无时无刻的焦虑坦然地讲出来。这种复杂性,让人们一边理解他、共情他,一边也会让人望“旸”兴叹——自己永远做不到像他这样的努力。
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对自我的怀疑一直在火了的刘旸身上缠绕着,他对界面文化说,自己经常会冒出一个念头——这辈子墓志铭上是不是只能刻《越狱的夏天》了?还有没有可能写出《越狱的冬天》?能不能再写出更好的东西?
他不相信失败的人值得被鼓励和认可
刘旸的童年,被“优秀”两个字紧紧包裹着。父亲是化学高级教师,母亲是语文高级教师,三岁时就认识3500多个字,他被冠以“神童”和“别人家的孩子”的称号。除了学习,父母要求他各个方面都要拔尖。他的成长轨迹,像一条直线,笔直而清晰。
学生时代,刘旸的生活几乎被习题填满。从早到晚,他的时间被切割成一块块,每一块都塞满了功课。中学时,卧室的飘窗边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练习册,他感觉自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练习册是那块永远推不到顶的石头。疲惫时他喜欢望向窗外,目光穿过“石头”,至少给他提供了一种想象到空间——等这些题都刷完了,就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等待刘旸的会是一次冷战,“考得越不好冷战的越久”。因此在他的人生观里种下了一个逻辑——只有优秀才可以得到父母的爱。有一次参加学校里的400米比赛,不擅长运动的刘旸一直在尾端,看台上的同学们对着他喊“加油”,但刘旸却觉得这应该是大家对他的嘲笑,他不相信失败的人值得被鼓励和认可。
被身边的人看轻,成为了少年时期刻在刘旸心头的一场噩梦。11岁时,他随父母从内蒙古搬到北京,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脱口秀的段子里,用幽默的方式解构了被北京同学们嘲笑“匈奴”“骑马上学”的羞耻感。这些言论,在一个内心敏感的男孩心底积压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直到成年后,他才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勉强与童年的自己和解。
儿时曾经的一部分快乐来自相声,小刘旸会把买来的相声磁带翻来覆去地听。美好的回忆一旦打开,当下的疲惫也能消除一些,如今刘旸会意识到,相声也带给他很多脱口秀段子中的创作灵感与写作技巧,当然二者也存在差异。不过当年,最先展现出来的是他的表演天赋。
有一段时间,刘旸喜欢模仿春晚里赵丽蓉的小品。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在家里表演《打工奇遇》的片段,却只换来母亲一句淡淡的评价,“要模仿就要好好模仿,认真研究认真学,得模仿得让大家都觉得好才行。”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一个小孩儿玩耍的天性。
不管是来自父母的冷水与冷战,抑或是刘旸想象中的对“加油”的不配得感,在他的童年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刘旸自称是个“社交低能”的人,他说他很少主动与人建立联系,甚至在心情极度郁闷时,也从未想过找朋友排解。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他几乎都断了联系。初中时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近几年两人加上了微信,但刘旸还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约对方出来,于是又渐渐疏远。
情感连接,在刘旸的世界里,权重占的极低,他的生活被高强度的工作填满。在小红书上,他分享了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先排定主要任务,然后见缝插针地把剩余事项塞进行程里。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说他“想红想疯了”。他在作品《越狱的夏天》里对此有所回应:“努力还有错了?”对他来说,努力,是一种让自己感到安心的方式。

他发现台下的学生们越来越难被点燃
“卷”“努力”“想红”——这些标签,指向了刘旸内心深处对一种高浓度“激情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毕业后将他引向了新东方。那时的他,怀揣着对教育行业的憧憬,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吸引他的,是那些名师身上散发的激情与才华。他记得同事宋浩的讲台上总是堆满了学生送的花,“这简直太神奇了!”回忆到这里时,刘旸的眼神再次充满火花。
刘旸当年的讲课视频如今在网上依然被流传,弹幕中不时飘过“发量惊人”和“我已经想笑了”之类的留言。他的喜感在那时已经显现。有一次去上班赶上北京的下雪天,刘旸在公交车上就开始琢磨如何编个开场能更吸引学生们。到了课堂上,他讲起南方人见到雪是什么样,北方人见到雪又是什么样,这种即兴的幽默瞬间点燃了课堂气氛。后来他也成为了很受欢迎的新东方老师,并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了不小的满足感。
在刘旸心中,自己课堂的核心精髓应该是励志,他追求用顶尖的方法,给学生带去巅峰的课堂体验。比如他会在某个学生灰心丧气的时候送上自己精心打磨的语录,希望可能点亮对方的生命道路。但后来他发现,当现实里的上升通道开始变得狭窄,自己的励志越来越起不到作用。
2015年起,刘旸开始参加“梦想之旅”——全国大中学生励志巡回演讲,接连的几年巡讲却让他倍感沮丧。他发现,台下的学生们越来越难以被点燃,“他们眼中的光芒很快就会消失。”刘旸回忆称,“比如讲到‘努力就会有结果’这句话,学生们不再相信。”无数次的冷场让他感到与学生的联结断裂了。“死灰一样的眼神是点不燃的,怎么励志呢?”从那时起,新东方老师这个头衔让他越来越没有成就感。
随着互联网教培行业的兴起,刘旸认为学生更加在意的是“幻觉”而非方法。那些不注重基础学习的“骗术”教学法大肆流传,他对整个行业感到灰心。对他来说,已经到头了。
他想做全国前十,而不是前一万
从一个百万年薪的新东方老师转行做全职脱口秀演员,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对刘旸来说,是经过缜密计算的。
早在转行前,刘旸在脱口秀领域的表现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2015年,他第一次站上了脱口秀舞台;2018年,他参加上海国际喜剧大赛,拿到冠军。以当时脱口秀线下专场的数量到门票的销量,他几乎已经跻身全国前十。他深知,要想在某个领域真正做好,光有信心远远不够,他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思考、精进,而不是被另一份工作分散精力。
作为一个典型的“J型人格”,2020年刘旸请同事帮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全职做脱口秀,2021年的收入会是多少?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底线——如果收入砍半,他还能接受,至少生活质量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朋友计算出的结果比砍半还要好一些。
辞职的决定得到了父母和妻子的支持。但最终让刘旸下定决心的,是黄执中的一句话,“如果我继续做会计,顶多是一个三流的会计,但是做辩论,世界上会多一个一流的辩手。”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旸。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按照市场推崇的方式教英语,他可能连全国一万名都排不上。但如果做单口喜剧演员,他非常有信心进入全国前十。
2021年,脱口秀综艺迎来了大爆发,但对刘旸来说,这一年却是备受打击的一年。由于一开始没有踩中线上综艺的档口,他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不红!如何形容这种感觉?他说,“孤独感快把人都吞噬了”。
像小时候一样,成年后刘旸还是非常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尤其是同行。有时,他会陷入极度的自我内耗,“我没有名气,同行会不会瞧不起我?”
一次去开放麦演出,当晚主持人介绍当天的演员时,调侃了五分钟刘旸不红,说北京四大脱口秀演员“石墨鹿教”——石老板、周奇墨、小鹿都火了,唯独刘旸教主没人知道。然而,当天线下的很多观众其实是看过刘旸专场的,他们认识他。这件事加深了刘旸的疑虑——他确实会被同行看轻。那五分钟里,底下的观众没有人笑。这次事件,刘旸在很多采访里提到过,但是他依然很气愤,说自己当时如同被炙烤,就像挨了五分钟纯粹的骂。

那段时间,刘旸去看了刺猬乐队的演出。在听赵子建唱《火车驶向云外》时,那句“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在年轻”一下子击中了他,让他感到特别悲伤,甚至绝望。他觉得自己像拼了命地奔跑,却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会先死还是先成名?我还有奔头吗?岁数不会等人的,人的努力要比岁数的消耗更快才行,我能赶上这个速度吗?”那晚,他喝得特别醉,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
事实上,那句歌词也是赵子健在最悲伤、最不想干的时候写的。骨子里对优秀极致的追求,害怕被人嘲笑,看不起,这些因素一致的推着刘旸下了决心——我得红一次。
于是,他开始参加《喜人奇妙夜》,更加努力地录播客,参加线下演出。他加倍努力用刻意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喜剧技巧。他不相信一瞬间的创作灵感,而是相信经过千锤百炼后,自己的技能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真正让刘旸蜕变的,是去学习了表演。这段经历最大的作用是增加了他的人生维度,帮助他的情绪恢复弹性,走出麻木,重新变得敏感起来。
刘旸记得,表演课上,老师会逼着大家去演绎别人的人生。有一个“星爷训练法”,是在黑板上写一些词,比如“温文尔雅”“古惑仔”“疯狗”,表演的场景是点菜,需要演出每种人不同的神态。在四个月的学习期间里,刘旸扮演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仿佛体验了很多次的人生。他记得老师李梅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人,你可以对价值有批判;但作为演员,你对所有的价值观只能去理解。”
比如,老师推荐的一本书里的女主角叫米尼。刘旸看完后,对主人公的举止怎么都无法理解。以前,他会觉得这个女人愚昧,想把她骂醒。但在老师的指点下,他意识到,如果要演她,就必须先理解她。
在体验过很多人的人生之后,再回到自己的人生,刘旸变得更豁达了。原来,人生有这么多可能性。他形容,如果说第一次转学到北京是在物理意义上让他暴露在更丰富的信息源中,那么这次表演课则让他在精神世界里大肆吸收了养分,学会了用更柔软的心态面对自己。
他希望儿子无论优秀与否都能得到真心的加油
终于,机遇开始又垂青于他。在《喜剧之王单口季》上,刘旸获得了第五名,而在《喜人奇妙夜》中,他斩获了最佳喜剧编剧奖,成为节目最大赢家。红了以后的刘旸,依然焦虑又痛苦。他担心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创作出好段子,担心今年是否就是他人生最高光的一年,担心是否能在作品上再有突破。现在写短剧,以后还能不能写电影、电视剧、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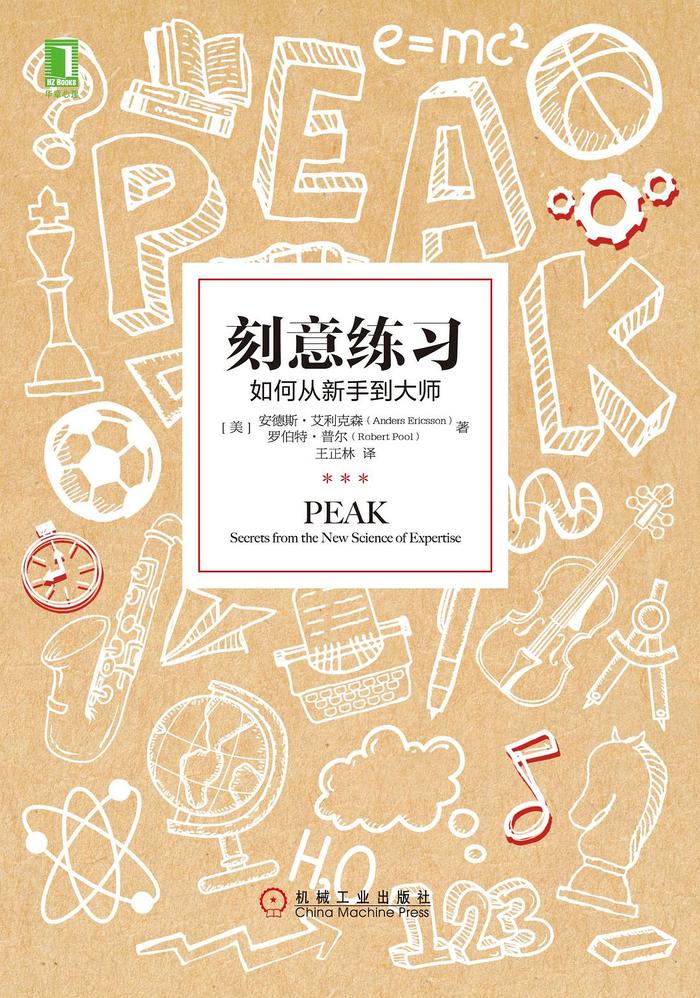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1
他依然很努力,刘旸信奉思维导图,相信一万小时理论,最喜欢《刻意练习》这本书。除了对作品的精雕细琢,就连录播客,他也在刻意研究规律,琢磨出梗的节奏。对他来说,播客、脱口秀、 Sketch,都是他练习喜剧表达的方式,只是在锻炼不同的“肌肉”而已。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刘旸同时做很多事,像是“想红想疯了”,但在他看来,他只是在做不同的表达,锻炼不同的能力而已。
他已经决定褪去一些敏感,不再像过去那样像“低压探测器”一样,害怕冷场,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参加《喜人奇妙夜》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开播的瞬间和《八十一难》大火时心情有所波动外,后面即使真的火了,心情也没有太大波澜。
刘旸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品本身。比赛时,他想的都是本子怎么写,开始不那么在乎外界的评价。“我2022年之前是刻意对批评麻木,只看赞美的话,2024年之后我对任何评价,包括夸奖都屏蔽了。”他对界面文化说道。
他也受到《喜人》里另一个演员土豆的影响,“土豆这个人痛苦,他每时每刻都痛苦,但他只为自己的创作痛苦。”刘旸认为,人这一生,应该有选择地只为一两件事痛苦。“要把痛苦的精力和能力都放在这一两件事上,这个很重要。”他不忘向记者叮咛着。

正式采访的那晚,是在北京东四胡同的单立人club,刘旸主持的第500期无聊斋节目《【见面聊聊】告别2024,祝你健康安宁得到不计其数的钱!》录制结束后。节目录制完毕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坐在工作室继续接受采访的刘旸带着天生理科生的精确,说他当晚录节目时喝了八瓶共4000毫升的水。工作人员问他累不累,他笑着说,比起之前每天说十几个小时,这都不算累。在一旁等待他的还有他的自媒体运营团队,采访结束后,他们还要补拍当天的素材。
如今,刘旸也成为了一名父亲。他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更有耐心了,对很多事都多了很多同理心。
在《喜剧之王》总决赛上,他准备了一封给儿子小野的信,表达了一个父亲最深的祝福:“我从小骨子里不相信一个不优秀的人能得到大家的赞誉,从那之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很努力的人,在我参与的各项领域都想做到最好,做不到最好的领域我压根不参与。我希望无论你优秀与否,看台上都会有真心的加油。我希望你可以不一样,也许不优秀也可以,也许被爱不需要资格,也许只要能开开心心的活着,就算是跑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是谁,为什么?
刘旸:Dave Chappelle、路易斯·C·K,他们在一些很重、很严肃的议题,能用充满脑洞的语言去表达,能化解掉,特别能调侃。路易斯·C·K会更奇葩一些。
界面文化:怎么看待脱口秀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繁荣?
刘旸:作为创作者肯定是诚惶诚恐的,因为现在这个繁荣会导致大量的观众每周都看脱口秀,但是大家的创作是跟不上的。一个月能有个五分钟的新段子都已经算是写得快的了。大家跟不上就会刷老段子,但是经常刷到老段子就会折损市场口碑,所以现在是有点发展太快了。
界面文化:需要不断找新的梗不断创新会是内容创作链条里最难的事吗?
刘旸:写新的梗不是最难的,技巧是最难的,技巧的提升会比寻找素材难得多。如果素材无限,但是每个素材都用同一样的创作处理方式,大家很快就会听腻。只要生活就会有素材,所以最难的还是结构的创新。
界面文化:是脱口秀好笑就可以,还是也需要在创作里加上一些其他价值?
刘旸:我觉得是好笑就可以,但是这两种谁也别评判谁,有的人是好笑中有点表达,高级了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纯为了这个去写我觉得也不太好。有些人会权衡,比如这个地方我是去发出声音更重要,还是在这儿完完全全变成梗了。我觉得是艺术创作的不同,我会比较倾向于变成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表达让人觉得很沉重。我喜欢的演员,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点到为止,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这是我眼中最好的。
界面文化:“标签”和“金句” 会困住你吗?
刘旸:这个会困扰我,因为线上就需要这个,线上就需要一个标签,才好传播,大家才能记住你。但是我也挺乐观的,我觉得人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喜剧技巧,不用标签、不用金句大家也能记住你,我觉得会有那么一天。
界面文化:预判一下脱口秀行业的未来?
刘旸:在悲观的层面上,我觉得世界在变坏,国外的单口喜剧现在好笑的真不多,经典的都在过去。不过在中国脱口秀行业还是越来越好的,因为还没有到行业的半衰期,现在还是呈放射状的开枝散叶,现在中国还没有做到每一个城市有一个俱乐部,但是几乎做到了每一个城市都有人说相声,每个大学都有相声社,所以脱口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远没有到鼎盛的时期,我们要为那一瞬间做好准备。
(本文按语部分写作:徐鲁青,文中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