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视频极速版下载安装:黑料门-今日黑料-最新海角-潘公凯复旦演讲: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怎么就成了艺术品?
编者按:艺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自然如此宏大,生命万般复杂,艺术或许是我们感受世界的一种最奇妙的方式。
2025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原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发表《现代艺术的边界》主题演讲,在探讨“何为艺术”的基础上,分析艺术作品与常态生活的边界之所在,提出对现代艺术边界问题的深度思考。
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探讨
此次分享是基于2013年出版的《现代艺术的边界》一书。现代艺术的边界问题,一直是被艺术家、艺术理论家们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想探讨这一边界问题,我们就要从“什么是艺术”说起。
“什么是艺术”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真正成为系统的哲学问题是在18世纪美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后。20世纪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进一步挑战了艺术的定义,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开放和复杂。
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是理式的投影,而艺术仅模仿现实世界,因此与真理隔了两层,所以具有欺骗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但强调这种模仿具有认知和净化功能,能够唤起情感。艺术不仅是再现,更是对人类行动的提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艺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是一种“无功利的愉悦”,它不服务于功利目的,而是通过形式引发纯粹审美愉悦。黑格尔将艺术视为“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和发展阶段之一,是理念(真理)通过感性形式的表达。是思想和感性的统一,艺术表现了时代的“世界精神”,但他认为艺术最终会被哲学取代。叔本华则认为艺术是意志的对象化,它让人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痛苦,通过静观理念达到超越,进入纯粹的审美体验。杜威也在《艺术即经验》中指出:艺术是经验的深化和重塑,日常生活本身可以成为艺术体验的一部分。克莱夫·贝尔更是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即线条、色彩等形式的组合引发审美情感,无关现实内容。
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维特根斯坦这里,上述一系列的传统理论受到了冲击。他认为各种艺术品之间只是属于“家族相似”概念,即艺术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重叠的相似性,艺术通过“相似性链条”联结,对艺术的定义只能依赖于语境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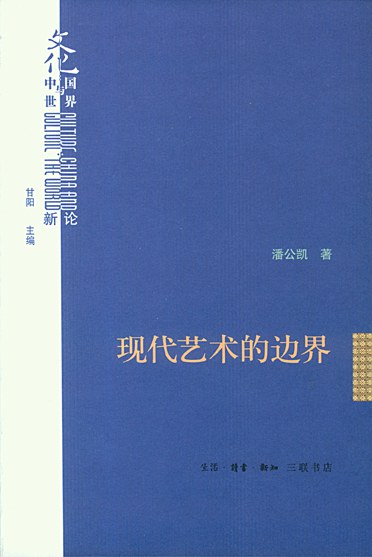
潘公凯《现代艺术的边界》书封
而当杜尚的现成品艺术被放置在展厅开始,传统艺术的定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颠覆和挑战,越来越说不清楚,艺术开始由艺术家群体的主观判断来定义,现代艺术理论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观念,而非物质形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的提法转向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问题。二十世纪下半期,边界问题成为争论的重点。其最重要的理由便是艺术品与生活现成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学家认为杜尚以后,艺术和美脱开了,艺术不一定是美的,美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艺术。主流美学界实质上是放弃了在本体论上对艺术作品的界定,艺术的解释权交给了一个运作机制,即“艺术界”。(这一机制由艺术史论家、艺术批评家、美术馆、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家本人等共同构成,他们讨论、判定哪些作品可以被称之为艺术作品。)
在此背景下,乔治·迪基提出了他的“艺术体制论”,即艺术是“由艺术界体制授予地位的人工物”,艺术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本体论界线依旧无法被认定。因此,汉斯·贝尔廷和阿瑟·丹托分别提出了“艺术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
“错构”概念的提出
1990年代初,我应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邀请到美国访问考察。当时我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已经敏锐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本质,所以我根据自己对西方艺术,尤其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的个人直观研究,得出了与当时的理论家们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当时大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究竟有没有边界。而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边界是确确实实,明明白白存在的,难题只是怎么来分析和论证这个边界,如何将其说清楚。
我在1993年写了一篇名为《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的文章,于1995年初发表于《新美术》期刊。这篇文章提出了名为“错构”的原创性概念。我认为艺术作品和非艺术作品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存在物和常态的现实生活的逻辑之网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此,我引入了一对概念:“常态”和“非常态”。在日常生活中,“常态” 即为我们的理性、经验、习惯的积累而习以为常的一切存在现象;“非常态” 则是超出我们经验范围,不能被我们在经验中所习得的常理常情所认同。“非常态”的存在因其特殊性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令我们新奇或困惑。
在极为粗略地考察了生活中的“常态”与“非常态”之后,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作出判断界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是一种“非常态”的构成。
艺术作品与常态生活中的其他事物的共性在于,它们都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说都是以一定的形态得以存在……但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日常生活是常态,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呈现具有人的理智和经验所认同的合理性——即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称之为合功利性。人的常态生活被组织在这种合目的性的逻辑之网中,这种逻辑之网提供了每一个时空单位中的常态生活所具有的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是可以在逻辑之网中被解释的。这个逻辑之网在这里具有关键性。所谓生活的非常态,正是相对于这个逻辑之网而言,是在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所认可的逻辑之网中显得不协调,显得错乱、悖谬的部分,它因此而从习以为常以至视而不见的逻辑背景中突现出来,引起我们感官的注意,引起惊奇和困惑。这种从正常逻辑背景中突现出来的不协调和悖谬,正是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将这种与常态逻辑背景的不协调和悖谬称之为非逻辑结构。
非逻辑结构有三种主要形态:错构、错置、错序。这三种非逻辑形态又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也可将三者统称之为“错构”,即错误的时空结构。
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欣赏,则不仅表现为形式构成上的非常态,而且表现为目的意义上的非常态。其一,它是由作者和观众自觉地有意识地被赋予意义的,意义在艺术品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其二,艺术品传达的意义与日常生活的逻辑之网没有直接的联系,是非功利非实用性的。因此,它会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之网上格格不入地突现出来,显得孤立和异样,而引起人们的注目与困惑。
艺术作品的“非常态”
非常态是对常态的否定。
就如“醉”是对“醒”的否定一样,艺术的审美的生活是对事功的实用的生活之否定——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此。艺术的源头、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界定,均在于此。
至此,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艺术品是生活的一种非常态形式,其必要条件是:形式的错构+意义的孤离。
马塞尔·杜尚的《现成的自行车轮》被视为现成品艺术的奠基之作。1913年,他将一个自行车轮倒置安装在厨房木凳上,最初仅作为 “消遣”装置。1916年,他正式提出了“现成品”概念,这件作品的内涵被重新定义,直指艺术的本质、创作权和观者的认知边界。杜尚将工业时代的普通物件翻转、倒置、组合为一个新的存在物,剥离其常态功能性,迫使观众以“非功利”视角审视它们。这件作品不仅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更重塑了人们对艺术价值与意义的理解。

马塞尔·杜尚作品《泉》,1950年(1917年原作的复制品)。
更为激进的是《泉》——杜尚从商店购买了一个小便器,署名“R.Mutt 1917”,放置于展厅。这一作品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艺术品的期待:当小便池出现在卫生间时是常态,但置于美术馆则成为非常态的存在。这种错置引发的关注和困惑,正是杜尚想要传达的核心: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统媒介或形态,而在于它如何与现实世界建立新的关系——通过呈现“非常态”的存在物,挑战人们对艺术的固有认知。这个存在物与周围环境的非逻辑联系(非常态)成为了这件作品得以成立的最基本要素。而这件作品又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提供了一种既有批判性又有开创性的价值指向:人类艺术的本质,不是由油画技术、雕塑技术及其所构成的虚幻其实所规定的,甚至不是由绘画、雕塑之类的传统形态所规定,而是由作为艺术品这一非常态存在物与常态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这便是杜尚的小便池的里程碑意义。
博伊斯的作品《导向力,1974》是一件接近艺术与生活边界的作品。1974年10月,他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型展览《艺术进入社会——社会进入艺术》中做了这样一件作品。他先是每天在展厅里和观众辩论,讲述他的“新社会的导向”。他的身边放了三个画架,上面放着黑板,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写完即将黑板丢在地上。连续讲了好多天,直到地上丢满了一百块黑板,连同一个幻灯机和一根拐杖,成了一件环境作品。这件作品粗看起来与常态生活很近似,讲演和辩论的用具——黑板和幻灯机,都是常用的。但仔细一想,其中的“非常态”还是很明显的,一百块黑板扔得满地都是,上面写的也都是乱七八糟的字句、图形。任何一位正经教授都不会如此演讲。这显然是一次由博物馆默许的演戏式的讲演,况且黑板也不需要一百块,以致都写不出什么内容了——形式的错构(非常态)依然是保障这一作品得以成立的要素。
艺术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常态”改变、破坏、拆解并重构,切断并脱开于常态的现实意义逻辑之网;使常态物改造为一个新的存在物与周边关系形成“非常态”的对照性结构,超出人的经验范围,向观者展示其中的不合理性;从而建造一个意义的“空缺”(意义的“空缺”是一个引诱和启示,观者会注意它,从而产生思考),并由艺术家本人(或留给观者)加入与现实逻辑之网毫无关联的“非常态”意义,使这些物品有成为艺术作品的可能,这一过程就是“错构”。

约瑟夫·博伊斯作品《油脂椅》,1964年。
这种判断就是我在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区分上,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的、全新的理论结构和逻辑判断。
但是,这个观点在之后的整整15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2011年,世界美学大会于北京大学召开,这篇文章引起了大会专家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一千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因为我的观点颠覆了阿瑟·丹托的观点。而阿瑟·丹托本人听说此事后,也两次邀请我去美国与他探讨这个艺术的边界问题。
至此,在认真思考、体会与总结之后,我将西方现代艺术的基本结构,概括为“错构”。将“错与不错”“怎么错”,看成是现当代世界观念艺术作品的基石和专业性之所在。“错构”这一界限是清晰且明确的。虽然这个界限在不断向外扩展,艺术作品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大,但艺术作品和非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将永远存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 26
26


 48158
48158 46
46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


 65573
65573 36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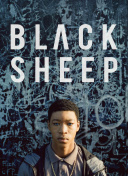 63128
63128 4
4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 78
78


 63524
6352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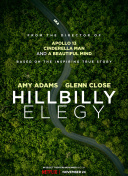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31856
31856 47
47


 71272
71272 50
50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94331
94331 53
53


 29063
29063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 44
44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89028
89028 4
4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


 62398
62398 1
1


 63428
63428 58
58


 63473
63473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46245
46245 22
22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 35
35


 45060
45060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42
42


 41857
41857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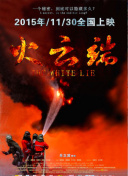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