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vlog破解版入口:半糖次元黄化破解版-从《束草的冬天》到《冷到下雪》:当记忆再现
资料显示,束草市是韩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位于三八线以南62公里处,城市面积100平方公里出头,人口不足10万。点开束草市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更详尽的介绍,这里对“束草”一词的解释是,一头睡倒的牛吃着捆束起来的草,束草市的形状就像这头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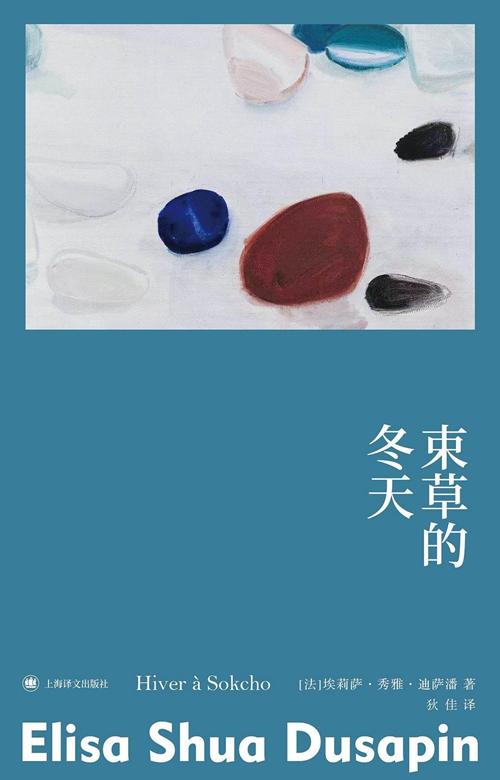
法国作家埃莉萨·秀雅·迪萨潘笔下,束草市有更具体的描述:海边施工的锚地,电影院拆除后的废墟,小巷里散发大蒜味道的下水道,港口和鱼市,“束草市沿海而建,朝鲜就在北面,离我们只有六十公里,带电的铁丝网像是一道伤疤,割开海岸线”。这都出自作家在2016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束草的冬天》。小说里,这个阴冷、孤寂,仿佛被世界遗忘过后蛰居在历史伤口的城市,一位年轻的女孩在民宿担任前台,她遇到了一位来此度假的法国漫画家,在漫画家的邀请下,女孩陪同他去寻找“真实”的束草。与此同时,女孩的生活逐渐表露,她无趣且看不到未来的工作,她与男友和母亲脆弱的关系,她扎根于此却依稀想要离开的愿望。最终,她将愿望寄托在漫画家身上——成为他笔下的一个角色。

《束草的冬天》电影剧照
环境的衬托下,经由女孩视角呈现的这个故事带有清冷的特质,无论是母亲、男友,还是民宿的老板和其他几位住客,人物如同剪影在女孩周围闪现,他们与女孩的交流并不多。也恰恰因此,凸显出女孩对漫画家特别的关注。当漫画家刚出现时,女孩就详尽描述了他的样貌和动作,“西方人的脸。深色的眼睛。头发梳向一边。目光从我身上穿过,并没正眼看”,漫画家叫亚恩·凯朗,出生于1968年的法国人,对女孩来说,他的出现不啻于一颗打破眼下庸常生活的石子,激起女孩的新鲜感和潜伏在身体中的久远记忆。女孩是韩法混血,23年前,她的法国父亲在束草的渔港与母亲相识,随后消失。
这似乎可以进一步解释女孩对漫画家的感受,他代表了曾经属于女孩却意外失落的那部分,在此意义上,与漫画家的交往等同于一次找寻自我。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女孩陪同漫画家深入这座城市的角落,揣摩漫画家言语背后的情绪和深意,漫画家则总是以疏离的态度对待女孩。女孩视角下的他更像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从这座城市和女孩身上寻找创作素材,即便面对女孩的多次追问,他都不愿透露是否会将这里看到的事物付诸笔端。

《束草的冬天》电影剧照
如果说,将这部小说仅仅看作是异国男女之间一次错位的情感触碰,多少有些偏离作家的用意。同样身为韩法混血,且在巴黎、首尔和瑞士都有过成长经历的作家本人对多元文化自然有着切身的感知,她笔下的人物关系其实暗藏着这种文化与身份差异背后的不对等,一位世界中心的外来者站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创伤的边缘地,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身处高位,可以自由地选择去看什么,选择接受什么、拒绝什么。再考虑到他的职业——借画笔创作故事的漫画家,创作自由再次赋予他权利,可以选择将束草的哪些部分以怎样的面貌描绘出来。

《束草的冬天》电影剧照
这也是为什么,不甘于沦为观察对象的女孩多次追问漫画家会怎样创作关于这里的经历,她甚至主动想象画家笔下的世界,以此来反抗这种身份带来的不平等,争夺自己在创作者笔下的位置。无论如何,漫画家最终都要带着他的故事离开,联想23年前抛下自己和母亲离开束草的法国男人,过去与当下的重叠加深了女孩抗争背后的愤怒,“他没有权利离开。没有权利带着他的故事离开。没有权利去世界另一端展示那个故事。他没有权利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让我的故事在岩石上干涸”。小说最后,当漫画家离开之前问到可以做什么来向女孩表示感谢时,女孩要求漫画家尝尝自己做的菜。在多次拒绝尝试女孩的料理后,如今他必须吃下这道危险的河豚刺身,这是女孩最直接的反抗:你带走这里的故事,也必须吞下并成为这里的一部分。

埃莉萨·秀雅·迪萨潘
仅仅依靠掠影般的人物和风光、短篇体量的篇幅,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就对基于地域、职业、性别等身份加持下的差异进行了如此微妙、看似柔和但又锋利的表达,这正是这位作家和这部小说的惊喜之处。此外,裹着纱布如幽魂般在民宿现身的整容女孩和为了去首尔工作准备整容的男友,这些渴望改变自我的角色有着跟女孩同等的困境,弥漫于束草的这种身份焦虑是漫画家不能体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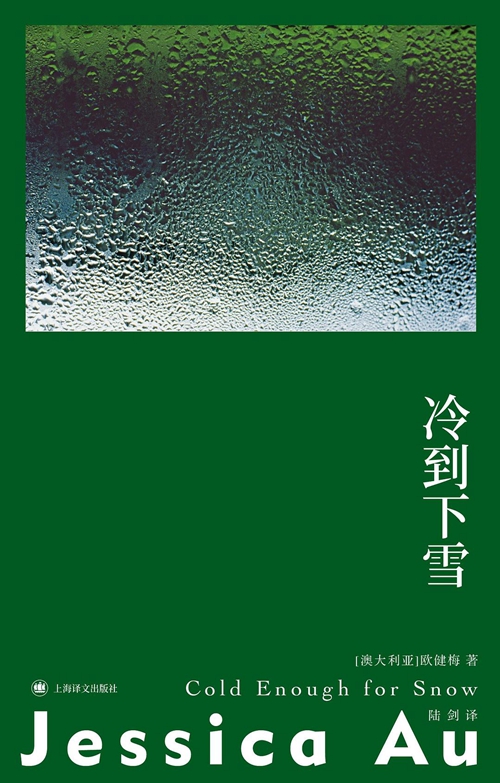
女孩和漫画家之外,小说在人物关系上着笔最多的部分是女孩和母亲,今天,当“东亚母女”这个词几乎固化为在对抗与和解间来回撕扯的情感模式,束草里的女孩和母亲却维持着一种低能量的关系。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欧健梅的第一部小说《冷到下雪》呈现了类似的母女关系,十月雨季的东京,一对母女从各自生活的国家来到这里,成年后从未与母亲相伴出行的女儿,希望在这趟旅程中填补这段空白。之所以选择东京,是因为对于曾在香港生活的母亲来说,亚洲城市更容易让她感到亲近。但也正如女儿提到的,自己之前来过日本,母亲没来过。这趟“让我俩都变成外国人,占据平等地位,获得同等待遇”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由女儿主导。
驻足博物馆、美术馆和书店的过程中,女儿时常向母亲解释这些艺术产物的背景和意义,并追问母亲对它们的看法,原本出于增进母女关系的东京之旅几乎变成女儿对母亲的单向输出。反倒是母亲总是保持谦卑和谨慎,她似乎自然地将自己归为这段关系里顺从对方的角色,即便是午餐时能替女儿指点菜单上不认识的字,都能让她“为终于能帮上点忙松了口气”。
小说里的女儿对待母亲的方式很容易让她为读者诟病,她被批评过于专横、自私,不考虑母亲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角色身上的道德瑕疵成为不少读者对这部小说恶评的原因之一。日本的最后一天,当母亲问起女儿的工作,后者用“原画复现”原理回答她,“即由于上面的颜料涂层变薄脱落,使得画家先前绘制的底层显露出来。有时只是很小的部分,有时颜料发生了变化,但有时会有重大发现,比如整个轮廓、某个动物或某件家具得以重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写作和画画如出一辙”。

欧健梅
作家在小说末尾点明女儿作为写作者的身份,提醒读者将旅途中的经历与写作者先前讲述的成长片段再次勾连。她曾在求学期间钦慕讲师,一度着迷后者象征智识与优越的生活方式,哪怕放置在讲师家厨房的蓝色小碗与自己平时的饭碗一样,在讲师博物馆一般的家里,这普通的小碗也凸显出截然不同的意味。餐馆打工的日子,她因此结识了担任“引导者”的男友,并习惯迁就对方。旅途中,跟母亲讲起男友时,女儿提到某次跟男友去美术馆,两人走过那些被男友夸赞很美的画作,内心并不认同男友观点的她,“先他一步走进一间莫奈展厅”。随后话锋一转,女儿从这段往事回到跟母亲对话的当下,“我告诉母亲,那里展出的正是这周早些时候我和母亲一起看过的那幅画”。
相同的美术馆场景让过去与现在两段类似的经历重叠,这是写作者笔下“原画复现”的时刻。女儿意识到当下这段旅程中的母亲其实正如同曾被男友牵着向前走的自己,她曾仰慕并努力融入的智识生活,如今变成自己想要灌输给母亲的知识、美学和思维方式。欧健梅的这部小说看似写一种秋雨弥漫中忽远忽近的母女关系,其实是女儿通过写作对自身的追问,追问过去的自己何以成为现在的自己。即便她不愿意附和母亲的看法,但母亲“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总是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经验还是在她的成长经历里得到印证,男友、导师,甚至餐厅里那个不顾及她工作、喋喋不休的男人都成为她的一部分。
至于母亲,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写到,外出归来的女儿发现母亲不在房间,询问酒店接待处的男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说没见过母亲,甚至表示我预订的是一人入住,不是两个人”。联系关于“原画复现”的对话最后,女儿告诉母亲“最好不要相信自己读到的任何东西”,这段与母亲共度的旅程或许是这位写作者虚构出来的。以此来讲,成年之后未曾与母亲相伴的写作者,察觉到他人留存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印记唯独没有来自母亲的,便在笔下创作出一个时刻包容自己的母亲,“母亲最后现身时,也像一道幻影。她的羽绒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呼出的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化成一团白雾,好似一个消失的幽灵”。
这道幻影,构成这部氤氲质地的小说最悠长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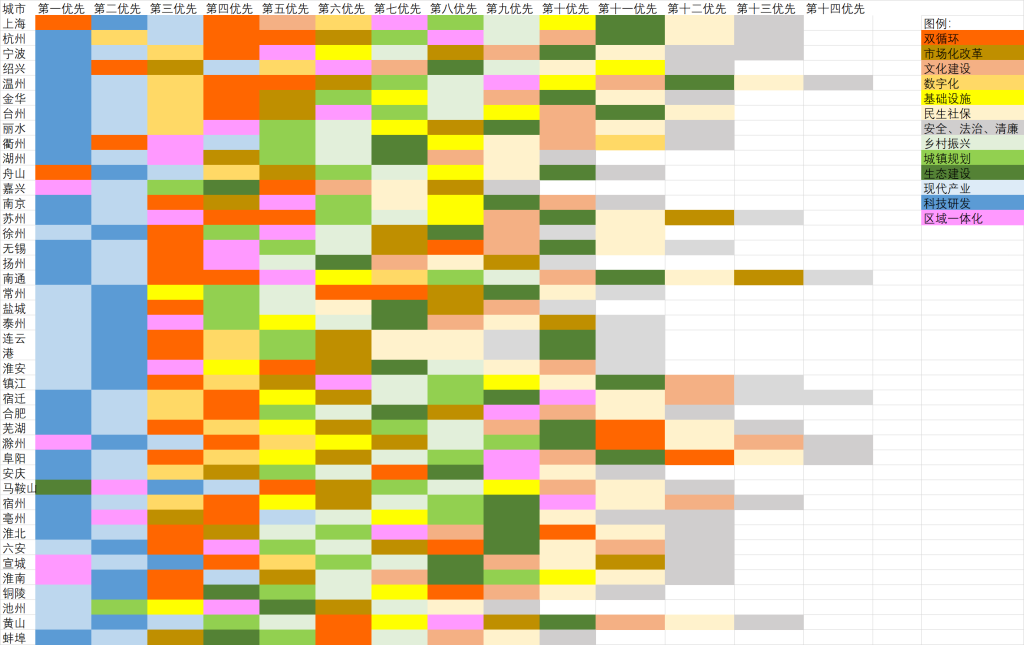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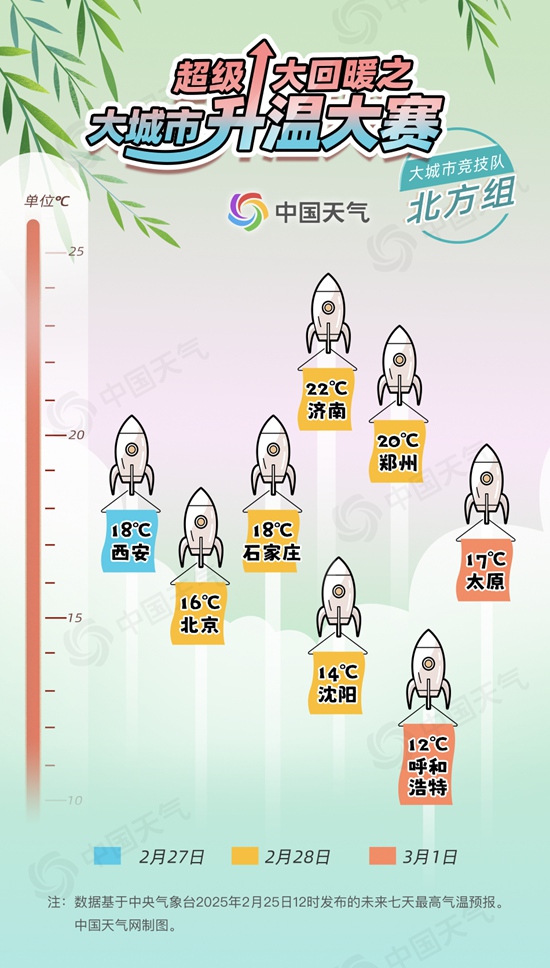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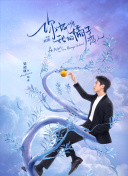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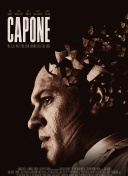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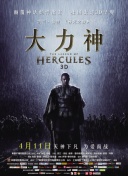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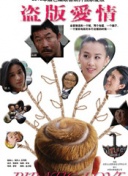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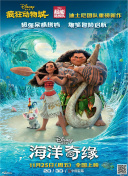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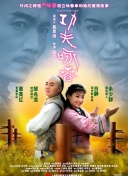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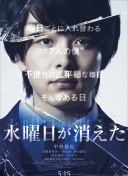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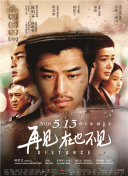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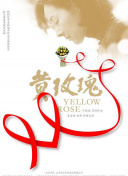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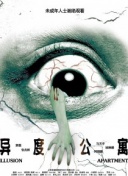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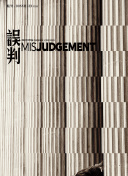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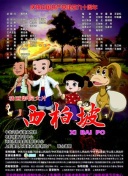 26
2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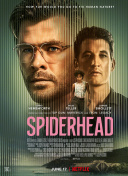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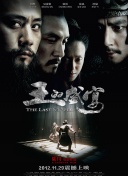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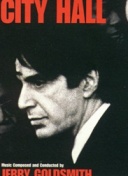

 48158
48158 46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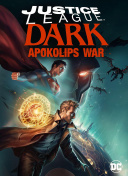 18095
180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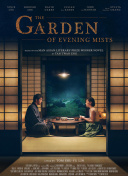 59
5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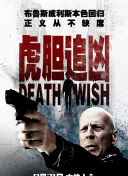


 76276
76276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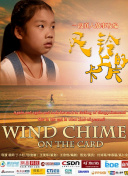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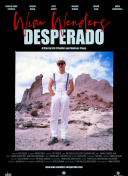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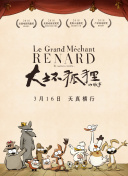 65573
655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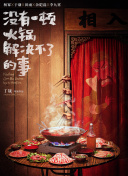 36
3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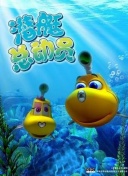


 63128
631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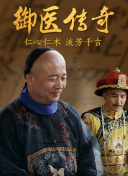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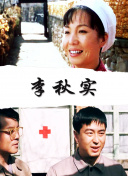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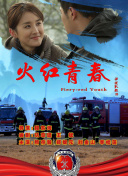

 30367
303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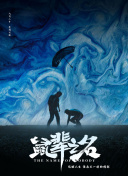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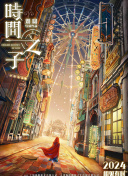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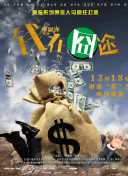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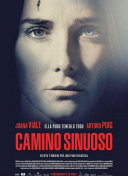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31856
3185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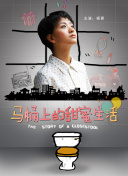 47
47


 71272
71272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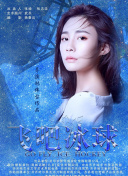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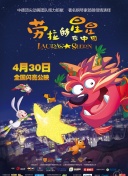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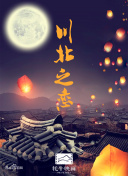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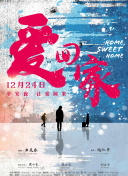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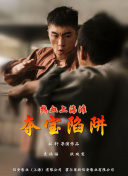

 94331
943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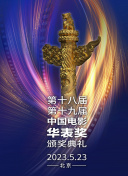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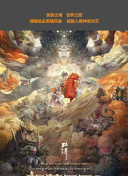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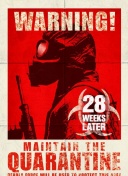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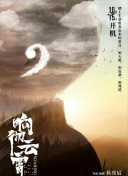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 44
44

 17391
17391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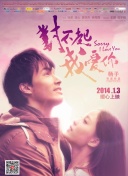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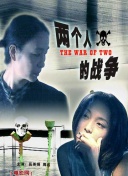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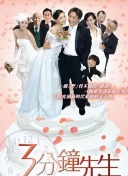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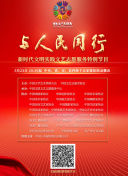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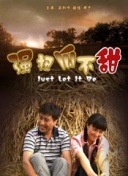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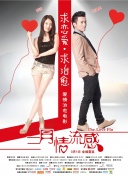 89028
890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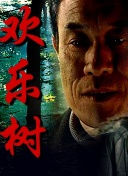 4
4


 98746
98746 8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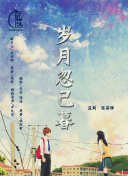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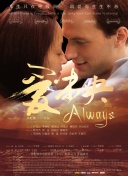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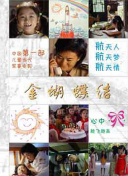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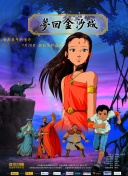 27017
270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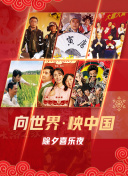 78
78


 54410
544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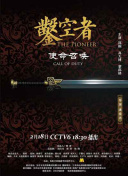 77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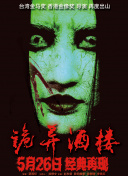

 62398
62398 1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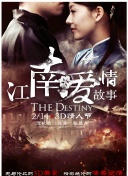


 63428
63428 58
58


 63473
634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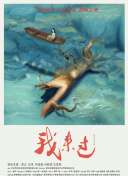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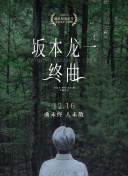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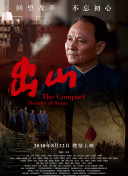
 46245
462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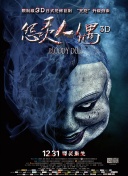 22
2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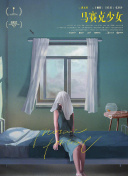


 19684
1968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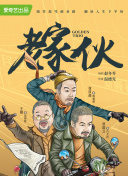 80
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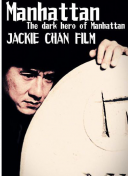

 22271
22271 49
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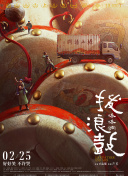


 94874
94874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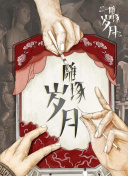

 36152
361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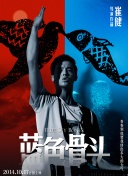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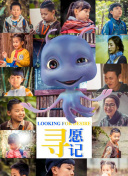

 45060
450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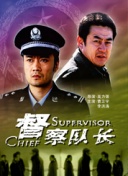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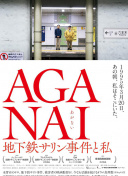 42
4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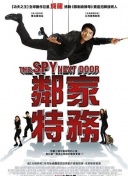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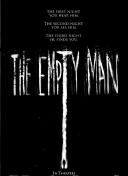

 41857
41857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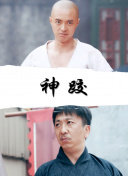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47534
47534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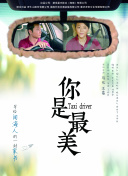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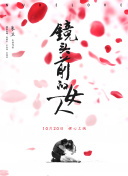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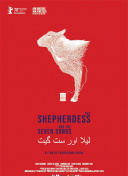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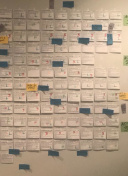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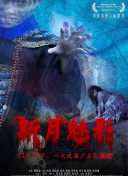 52980
52980 33
3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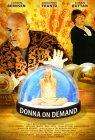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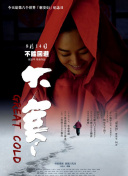 50061
50061 60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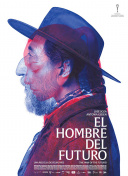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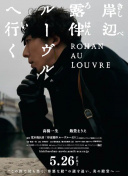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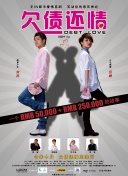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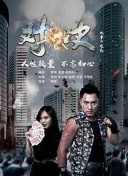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