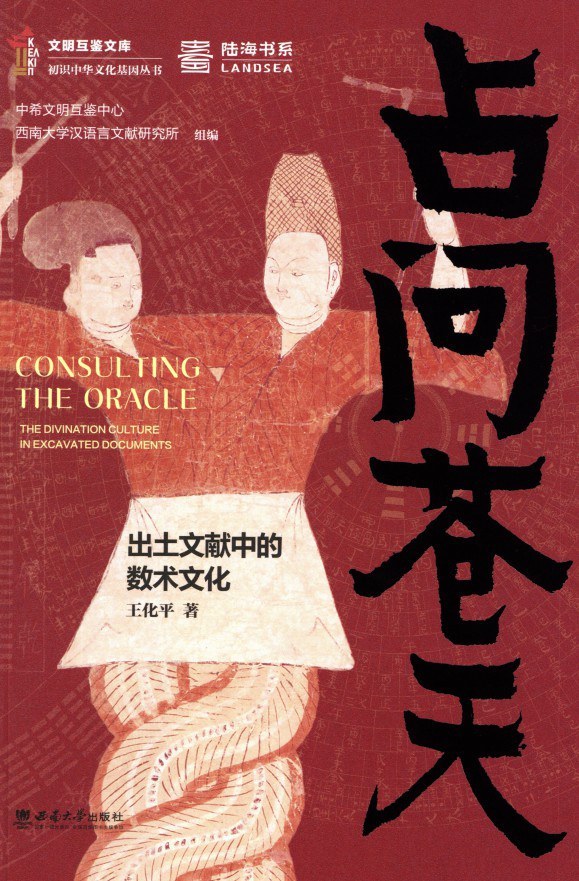黑料吃瓜网:糖心vlog是真的吗-吴铮强:作为宋代文化遗产的西湖十景
西湖:从杭城水源到游赏之地
作为中国传统园林景观巅峰之作的杭州西湖主要是南宋时期的遗产。
西湖是钱塘江入海的湾口处由泥沙淤积而成的潟湖。秦时还没有西湖,杭州市区和西湖一带是钱塘江的入海口,一片江海相连的浅海湾。那时的人口集中在现在灵隐寺东边的山谷,钱唐县治就设在此处。东汉末期钱塘江口泥沙不断堆积,慢慢形成了一片沙洲。居住在钱唐县东部的百姓时常被海水侵袭,不得安生,郡议曹华信主持修筑防海堤塘,原来的海湾由此变成一个湖泊。隋唐时,原来的沙洲与海塘经过反复冲刷堆积形成陆地,居民聚集形成聚落,杭州在这时期开始设立,州治建在凤凰山下,这应该是杭州建城的开始。这时的西湖仍称“钱塘湖”,随着城市在湖东逐渐成形,白居易开始称钱塘湖为“西湖”。
由于城内常受钱塘江咸水入侵,这时西湖的主要功能是为杭城百姓提供淡水水源,所以才有李泌开凿六井。白居易出守杭州时,他在西湖(上湖)与下湖之间修筑了一条白沙堤,用来调节西湖水位、解决农田的灌溉问题。唐代白沙堤在宝石山东麓,随着下湖的消失,白沙堤已经不存,后来杭人将连接孤山的湖堤称为“白堤”以纪念白居易。白居易还写下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这样著名的西湖诗句,西湖在白居易眼中已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直到这时,西湖的主要功能仍是提供饮用水与灌溉水源,西湖山水也保留着朴野自然的风貌,并无铅华媚态。北宋的苏轼修筑连通南北的长堤时,在堤上遍植桃柳,形成“苏堤春晓”标志性的桃红柳绿的景观,他在湖中设立的三座小石塔后来也成为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但无论苏轼如何将西湖景观化,无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如何将西湖景观意境化,苏堤与三潭本身都是功能性的工程,而非单纯的园林景观项目。
只有在南宋,西湖才在整体上成为都市人群游赏的对象。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杭州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当时最富贵繁华之地,有“销金窝儿”之称。在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与国家羸弱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西湖成了芸芸众生安逸享乐的温床。在南宋人眼里,“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南宋的西湖是临安百姓玩乐、节庆、笙歌、礼佛的公共园林,与杭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比如宝庆三年(1227)上巳节有一次非常轰动的游乐活动,知临安府袁韶“招从班十三人修禊事于西湖”,那日游赏西湖的情形真可谓繁复而尽兴:
今日之游,群贤毕至,举觞张圃之池,舣棹苏堤之柳,谒先贤之祠,仰千载之风。羽衣蹁跹,抱琴而来,弹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云》之操。已而联辔孤山之馆,引满海棠之下。是日也,晓烟空濛,昼景澄豁。睹物情之咸畅,喜春意之日新。却弦断管,一尘不侵。越嶂吴山,尽入清赏。凡贩夫所粥,毕售于公。左右游桡,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观也。于是乐甚献酬,交举或哦坡仙之什,或论晚唐之诗。颓然西景,放舟中流。
游赏已经成为南宋时杭州西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于是皇室与达官贵人纷纷占据湖山修筑园林,艺术家们更以西湖山水入画、入诗,并创造出西湖十景的题名,从而又完成了杭州西湖园林化、景观化与意境化的进程。西湖十景不但是这个进程的最终结果,并且在南宋以后进一步升华为特定的文化与精神的符号。
南宋西湖的景观化
南宋时皇室与达官贵人纷纷在西湖四周占地修建富丽精致的园林,结果杭州西湖在整体上构成一个巨型的园林景观。
南宋时皇家园林遍布杭城各地,其中西湖边有聚景园、屏山园、四圣延祥园等。聚景园是宋孝宗致养之地,光宗、宁宗也经常光临,西湖十景之“柳浪闻莺”即指此园。聚景园地处西湖东南,规模十分宏大,东起流福坊,西邻西湖,南至清波门,北至涌金门。此处可全览湖山之胜,将孤山、北山、苏堤、西山及保俶、雷峰诸塔尽收眼底。园内有景观建筑会芳殿、瀛春堂、揽远堂、芳华亭、花光亭(八角亭)及柳浪、学士二桥等。聚景园四季有景,《咸淳临安志》就形容“夹径老松益婆娑,每盛夏芙蓉弥望,游人舣舫绕堤,外守者培桑莳果”,又有瑶津、翠光、桂景、艳碧、凉观、琼芳、彩霞、寒碧、花醉、澄澜等名目。
《武林旧事》记载了孝宗邀太上皇与太上皇后一起游览聚景园的盛况。在遍游聚景园各景之后,太上皇等又坐船游湖至断桥,孝宗在游船上为太上皇、太上皇后祝酒。高宗在断桥上还遇见了“卖鱼羹人宋五嫂”,她对高宗说自己是“东京人氏,随驾到此”,高宗把宋五嫂请上船,“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还允许她向皇宫提供宋嫂鱼羹,“仍令后苑供应泛索”,这就是杭州名菜宋嫂鱼羹的来历。这一次赵构玩得特别尽兴,返程时已经喝醉。孝宗奉侍高宗游览聚景园引起杭州全城轰动,大家都赞叹孝宗的孝顺,时人为此填词《壶中天慢》,其中就有“两世明君,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之句。
南宋时孤山有四圣延祥观与西太乙宫两座道观,四圣延祥观奉祀紫微北极大帝之四将,即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大元帅真君,西太乙宫则供奉太乙十神真群。在两个道观之间又有皇家园林四圣延祥园。延祥园位置极佳,南宋时即有“西湖胜地,惟此为最”“此湖山胜景独为冠”的说法。延祥园以林逋墓为核心,内有黄庭殿、香月亭、六一泉、陈朝桧等景观。黄庭殿是一座多层建筑,可俯瞰西湖,为全园主体建筑,殿内有著名画家萧照的山水画。香月亭在林逋墓侧,旁环植梅花,亭中大书“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六一泉是孤山一处泉井,苏轼为纪念恩师欧阳修而命名“六一泉”,并于泉上建石室,南宋末年重修其亭,以太湖石为柱梁。
此外,南宋时净慈寺后也有皇家园林屏山园,开庆年间屏山园扩建,范围延伸至雷峰山下,理宗时更名为翠芳园。屏山园“内有八面亭堂,一片湖山,俱在目前”,是南宋观赏湖景的另一处胜地。
南宋时西湖四周遍布达官贵人的园林。其中出钱塘门往西湖北山一带,有古柳林和王杨存中的云润园,九曲墙下嗣秀王赵伯圭的择胜园,附近鄜王刘光世的隐秀园、玉壶园,昭庆寺(今少年宫)侧的谢太后府园。断桥附近有内贵张太尉的总宜园、杨存中的水月园、嗣秀王赵伯圭的秀王府园。往西至葛岭中段有权相史弥远与贾似道的园林,前者称琼华园、半春园、小隐园,后者称后乐园、养乐园,贾似道还占据了西泠桥南孤山一带的水竹院落。此外葛岭一带有赵婉容的快活园、廖莹中的寥花洲园,近苏堤又有裴禧的裴园,水仙王庙前杨驸马的挹秀园、刘光世的秀埜园等。再往西至赵公堤则有乔幼闻的乔园、史徽孙的史园及适安园(万花小隐园)。如果往西深处到九里松一带,又有尚书苏符的香林园、蕲王韩世忠的斑衣园。从九里松折返稍南至大麦岭一带,则有内侍卢允升的卢园、杨存中的梅坡园以及福王赵与芮的小水乐园。
出涌金门往西湖南山一带,除皇室的聚景园与屏山园,又有柳洲寺侧杨存中的环碧园、养鱼庄,万松岭内侍王氏的富览园,长桥南御赐的韩侂胄南园,雷峰塔一带循王张俊的真珠园、内侍甘昇的湖曲园,九曜山方家峪一带(今太子湾公园)有内侍刘公正的刘氏园,南高峰下还有最后为贾似道占有的水乐洞园。
权臣韩侂胄的南园、贾似道的后乐园原本都是皇室御园,后来就成为最奢华精美的私家园林。不过对于西湖的景观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任何单体园林的华丽雅致,而是足够的密集度让西湖本身成为一个巨型的园林。
西湖景观的意境化
南宋时期西湖四周遍布园林,奠定了西湖的景观基础。但是西湖十景的定型,还需要这些景观完成一个意象化的过程。
西湖景观的意境化,主要体现在西湖十景的提炼与西湖诗画的持续涌现。“西湖十景”题名最早出现在南宋文献,是绘画因素与风景审美创造性结合的产物。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西湖“山川秀发,四时画舫遨游,歌鼓之声不绝。好事者尝命十题,有曰: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两峰插云”,这是“西湖十景”在文献中的首次出现。吴自牧的《梦粱录》进一步指出,西湖十景是作为绘画题名而出现的:“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麴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
“西湖十景”的单个景观在北宋时期已见于画家笔下,如明人《天水冰山录》中称,宣和年间的翰林待诏张择端画过一幅《南屏晚钟图》。南宋迁都临安,精于书画的宋高宗也喜绘西湖山水图,元代庄肃《画继补遗》记载宋高宗:“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予家旧藏小景横卷,上亲题‘西湖雨雾’四字。”绍兴十六年(1146),宋高宗在南山万松岭麓重建画院,这里环境清幽,毗邻西湖,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西湖图景绘制之风,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湖十景最初就是南宋画院考试中出现的考题。此后陈清波绘制了《三潭印月图》《苏堤春晓图》《断桥残雪图》《曲院风荷图》《南屏晚钟图》《雷峰夕照图》,刘松年也有《西湖四景图》。南宋中后期,西湖十景已经成为完整、固定的绘图题材,出现了马麟的《西湖十景册》与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册》,李嵩的《西湖图》则从皇城的视角绘制了西湖全景图。
现存传为南宋的西湖图包括刘松年《西湖四景图》、李嵩《西湖图》、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西湖清趣图》以及叶肖岩《西湖十景图册》。刘松年是绍熙年间(1190-1194)的画院待诏,因居于俗称“暗门”的清波门附近而人称“暗门刘”。《南宋院画录》著录刘松年西湖山水图多幅,其中《西湖春晓图》被誉为“笔法秀美,设色古雅,堪与赵千里《桃源问津卷》相伯仲”。《西湖四景图》又称《四景山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浅设色,每幅纵
约41厘米、横约69厘米。此图撷取桃花垂柳、纳凉水阁、秋山红叶与松柏雪竹作为季节景观,描绘湖畔春行、纳凉远眺、虚堂闲坐、骑驴冒雪等西湖四季人文景观。组画将四季特征与人物活动融合得极为妥帖,近中景物描绘细而不拘,远山与湖水则以虚旷笔墨略约带过,极具西湖山水、亭园、人物情致,显示了画家对西湖景观的细致体察与深湛表现功力。
李嵩是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纸本水墨《西湖图》归于李嵩名下。《西湖图》纵27厘米、横80.7厘米,画卷中烟云明没,山色依稀,气势旷远,在一片湿润淋漓的雾霭下面,西湖边上的宝塔、桥垣、扁舟、楼亭,还有环湖的群峦,慢慢显出轮廓。画家采用了全景画法,似著身空中,俯瞰而下,巧妙地将个别景致略加调整,以求更合于构图韵致,使保俶、雷峰两塔遥遥相对,诸名胜奇景尽收眼底。画幅正中央,是群山环抱的外湖,亦是经意留出的空白。湖上风吹涟漪,浪遏飞舟,虚实相映,处理精到。近景湖滨上,用坚挺的界画笔法勾出楼阁屋宇,自左向右一字排开,形断势连,从而挽住湖水,使其显出回旋之势;也为全画空间层次定调妙笔。湖的左边,在散点叠染绘出的树丛之上,雷峰塔脱颖而出,塔下楼宇遍布,行笔纤细沉着。湖的右边,跨过断桥白堤,是孤山景色。此处笔调略虚,树丛皆以湿笔积染而成,浓重郁茂,得其生气。从孤山隔湖右望,画家以凝练之笔,纵横运转,写出层层亭阁。其后,山林掩映,笔法为破墨点染,浓淡相宜,并渐与湿笔抹出的远山融汇为一。
画幅远景的处理别具匠心,十分精彩。屋楼亭阁,只简笔表其形;竹林峰峦,亦淡墨略出其意;中留空白,实为烟云之路。所以笔墨无几,而气韵万千。及至湖水彼岸,那苏堤春晓景点之上,画家只略写五桥,随即深入远景刻画。用笔长驱直入,挥洒自如,于经意不经意之间,以看似杂乱之枯笔画出峦上远树,再以俊逸湿笔染出迷蒙的远山,将天高湖远、云锁雾罩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纵观全图,山色与笔墨同行,湖光与灵气俱化。这里有板实的楼台、宝塔,有沉郁的峰峦、丛树,还有空灵的烟波、云气,种种要素合于一起,结体自然,巧契天机,使人如亲临其境,不觉悠然神往。这种高度写实又极富变化的绘画作品被认为是南宋画院大师的艺术本色。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西湖图》创作于吴门画源兴起后的明代中期,画幅尾部有一极小款识“李嵩”是伪款。
《西湖清趣图》总长竟在16米,是现存唯一以描绘环西湖宅邸、店铺、街道等城市景观的画作,虽然被认为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苏州地区。但也有学者指出,从西湖印象、城门形制、桥梁道路、湖堤水闸、防火备警、引水工程、酒楼广告、舆服风尚、王府仪制乃至园林景观等图画细节出发,参照相关文献和考古实证,《西湖清趣图》所表现的应该是南宋晚期的西湖人文景物,即便是明代或更晚的作品,也应严格参考了早期的“粉本”。
至于《西湖十景图》,虽然南宋的僧若芬、马麟、陈清波等人都曾画过,现存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署名叶肖岩的一套《西湖十景图册》。此册画风为马夏一派,笔墨较为粗疏,所绘景观未必是西湖实景,但内容确凿无疑就是西湖十景,特别是两峰插云与三潭印月,南、北高峰上两座佛塔与湖中三座小塔赫然在目。
除了西湖景观图与西湖十景的命名,南宋也出现了吟咏西湖十景的组诗、组词,包括著名的王洧《湖山十景诗》与周密《西湖十景词》。诗词、绘画、题名的结合,说明西湖十景在南宋已经完成了其意境化、意象化的过程。
意象化意味着具体的物质形态升华为特定的精神文化的理念与意识,从而积淀为文化基因,超越时空地流传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沧海桑田,世事无常。元代侵占西湖的现象愈演愈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提到,苏堤以西的内湖,高处变为田地,低处变为鱼塘,苏堤东侧也被围垦和杂草占据,仅剩一条狭窄水道。因此明代不少杭州官员都提出疏浚西湖,正德三年(1508)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整治西湖,疏浚出的淤泥变成了杨公堤。这时南宋时期西湖周围所有的园林景观早已烟消云散,但今天的西湖仍然延续着南宋时西湖十景的景观格局。这是因为南宋时期西湖景观完成了一个意象化的过程,并且凝聚成杭州最重要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通过文献的传承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财富,并以此后的历史中不断地重生、更新、发扬光大。
西湖梦寻与十景重建
南宋灭亡后,作为实物的西湖景观虽然时兴时废,作为意境的西湖景观却不断深入世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南宋以后两次亡国,杭州作为都城,其都市繁盛与湖山美景更成为一种文化标记与故国情怀而深入人心。元初出现了《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追怀临安城的遗民作品。元朝刻意破坏南宋皇城与西湖景观。到了明朝,西湖景观不断有所恢复,而且逐渐取代临安成为士大夫追怀宋文化的特殊符号,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就在这种背景下形成。《西湖游览志》表面上看是一部记述西湖景观的说明书、西湖游览的指南,事实上其记述西湖景观时多追述宋朝历史,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向宋文化致敬的书。这一点清代的四库馆臣就已经指出,《四库全书总目》称《西湖游览志》“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故于高宗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到了清初,张岱的《西湖梦寻》不但进一步为西湖注入了故国情怀,更以“梦寻”的名义进一步升华西湖意境。张岱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他出生于官缨世家,兴趣广泛,博览群书,早年纵情于游乐,曾自撰墓志铭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崇祯八年(1635)张岱参加乡试不第,此后放弃科考终生不仕。明朝灭亡后张岱坚定抗清,但在南明政权趋于覆灭之际避兵剡中。此后张岱一心著述,生活清苦,“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被举为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既是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儒士,又是喜繁华尚奢侈的纨绔公子;既是慷慨激昂的义烈之士,又是明亡后苟且偷生的前朝遗民。《西湖梦寻》是康熙十年(1671)张岱以明朝遗民的身份写成,全书七十二则,第一则总写西湖外,共记述七十一处西湖及周边的名胜。张岱自幼跟随长辈在西湖别业生活,对西湖山水十分熟悉。可以说西湖本是张岱的西湖,他与三五人独享过冬日雪后西湖的孤寂与宁静,偏爱七月的夜西湖月色下的凉意。当西湖山水遭遇战火的浩劫,张岱便在梦中追寻西湖。西湖累积了千百年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都有说不尽的人文风情。西湖就是一座中国文化的陈列馆,任何一处景观都独立构成一部文化史。无论是祠堂陵墓还是道观佛寺,张岱的《西湖梦寻》总能翔实介绍各景点的创建及兴废经过,既有纵向的史实的梳理,又有横向的空间的叙述;既是一部西湖志书,又是一部感性的中国文化史。所以有学者指出,张岱“为西湖各处景致注入新的精神和内涵,提升了其文化品格,让它更有灵性,也更有气质,张岱也成为西湖风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彼此相互成就,张岱因西湖而不朽,西湖因张岱而生色”。
张岱年轻时发现并砸毁了毁灭临安城、宋六陵与西湖景观的元僧杨琏真伽的塑像,他是明朝遗民、抗清志士、江南士大夫的文化代表,《西湖梦寻》是他追怀故国、从文化上抵制清朝的著作。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以帝国之力再造即使明朝也没有完整呈现过的南宋西湖十景,便是他们征服在文化上特别自负的江南士大夫的最好方式。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圣祖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在江南一路游山玩水,不但为西湖留下了众多题咏,还御题西湖十景。玄烨将“两峰插云”写成“双峰插云”,改“麹院荷风”为“曲院风荷”,“雷峰夕照”变成“雷峰西照”,“南屏晚钟”则成了“南屏晓钟”。这次御题西湖十景就成为再现南宋西湖景观的契机。南宋的西湖十景往往没有具体的地点,只是画家、文人的艺术表现的一种意象,但安置康熙的御碑既需要确切的位置,又需要对应的景观。比如平湖秋月原来只是泛舟赏月,为了竖立御碑,高士其在白堤旁迁走寺院建造观月平台。柳浪闻莺的柳树在清兵入杭城时早已砍光,高士其特地在清波门附近密集种植几百棵柳树重建“柳浪”的景观。麹院荷风的麹院,元代以后就已衰落,康熙改成“曲院风荷”之后,李卫便建造九曲通幽的院落刻意迎合。
因康熙御题西湖十景而再造西湖景观,可以说是后世第一次整体性恢复南宋西湖景观,此举包含着“征服”汉族文化的意味。但清帝如此痴迷于西湖景观,康熙之后乾隆再下江南,不但为西湖十景各题御诗,还将西湖十景移植到圆明园等京城的皇家园林,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理解为清帝深受宋文化的影响。所以清代西湖十景的重建与复制,既是对宋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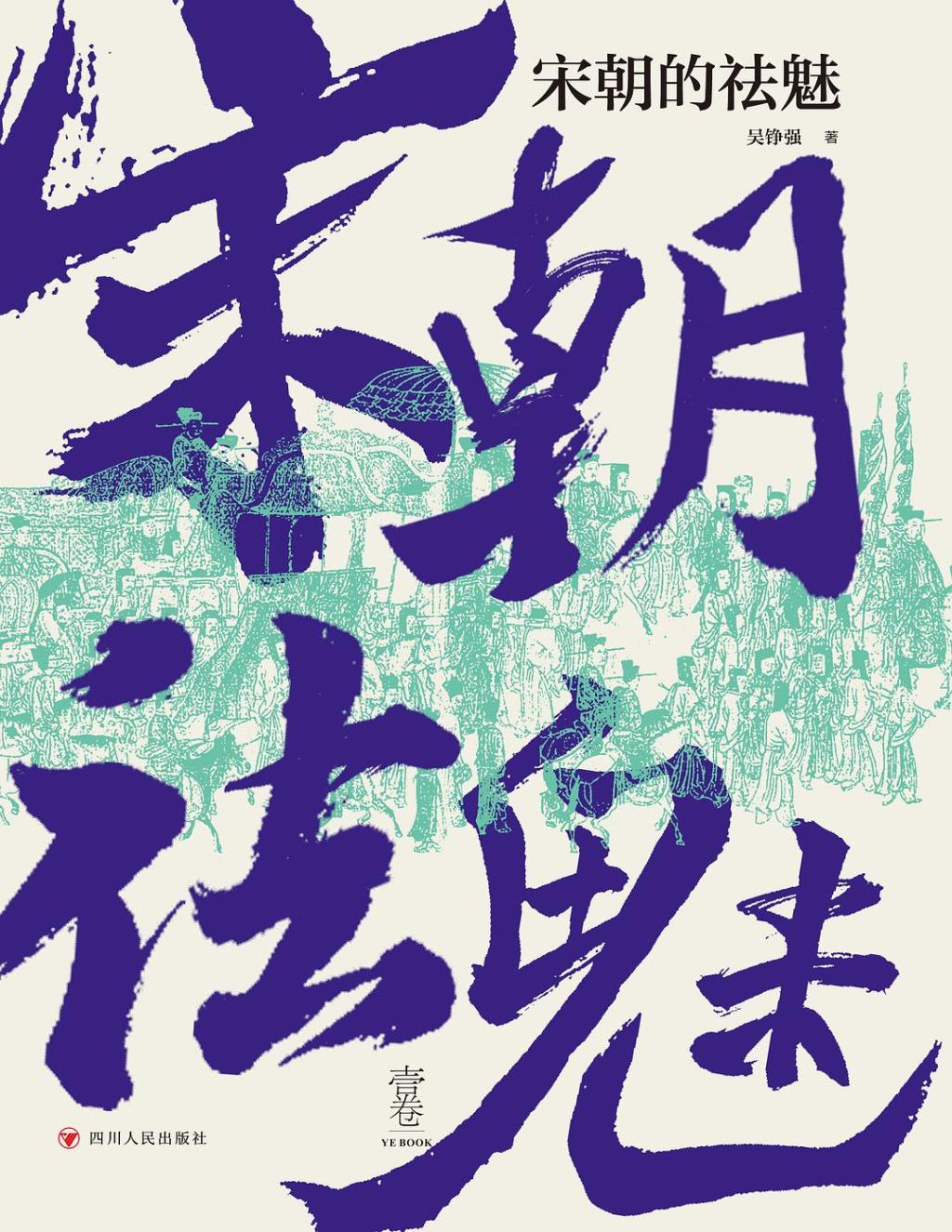
(本文摘自吴铮强著《宋朝的祛魅》,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