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琬评《失踪孩子档案》|女性成长与小说的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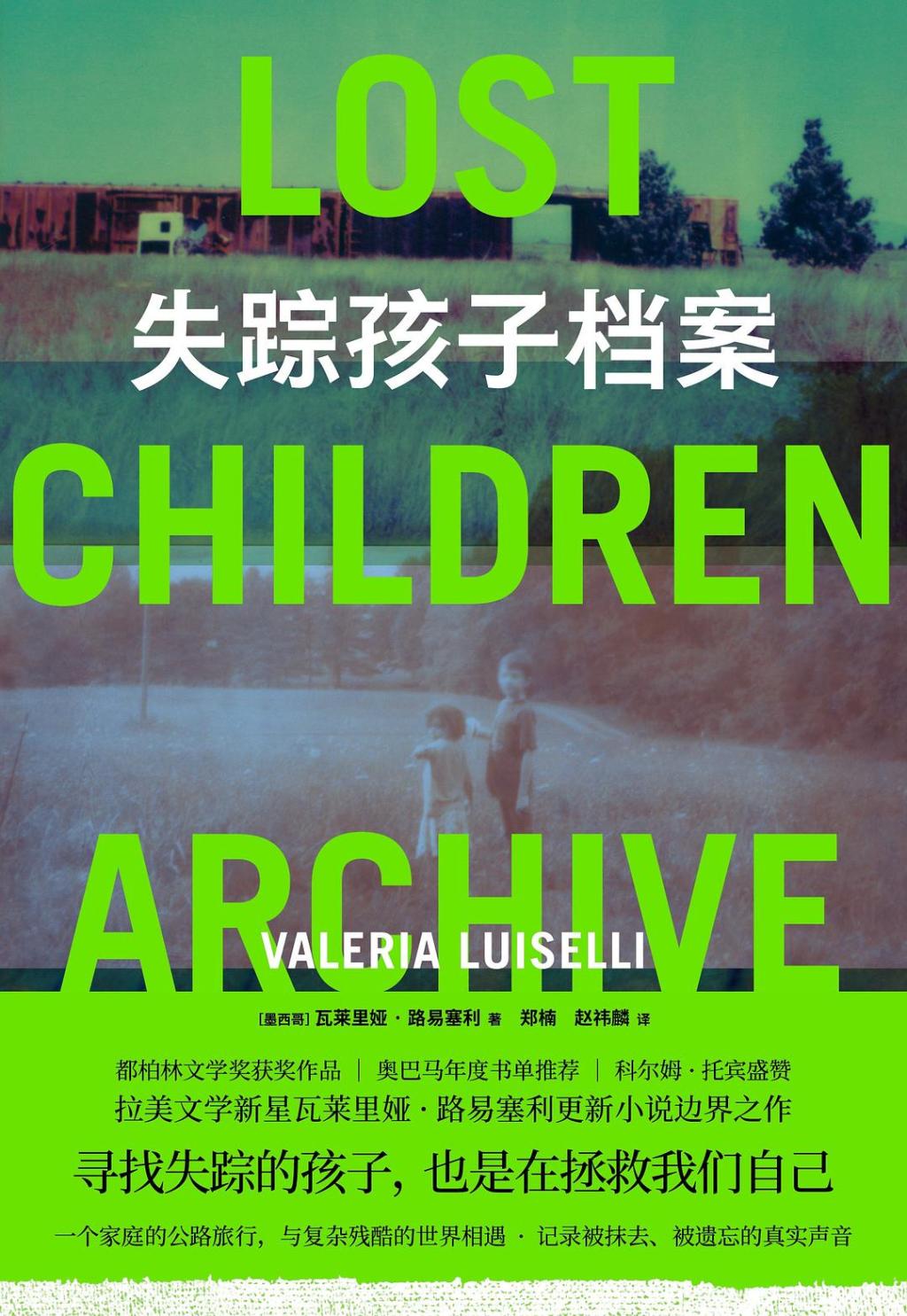
《失踪孩子档案》,[墨]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著,郑楠、赵祎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1月出版,432页,69.00元
《失踪孩子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是为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赢得2021年都柏林文学奖的作品。小说最初的写作动力,来自作者面对美墨边境难民儿童问题时感受到的愤怒和失望。此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19年,无形中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特朗普政府修建边境墙计划的批判和讽刺。其实作者早在奥巴马时期的2014年便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而那一年正是美国西南边境无证件移民儿童人数激增的一年。
这部小说在主题与形式上与路易塞利更早出版的散文集《假证件》(2010年)以及小说《没有重量的人》(2011年)有所重叠,它们都关注空间与迁徙,并能运用众多不同性质的材料,如新闻、日记、回忆录、档案、过去的文学文本等等。《假证件》在精神上共振本雅明、布罗茨基和康拉德,作者的目光穿梭于墓地、河流、工地、房间,捕捉各类都市空间对人类情感的形塑;《没有重量的人》以贴近路易塞利本人的女主人公为叙事者,将她的生活经历与真实存在的墨西哥诗人希尔韦托·欧文的人生平行起来。2013年路易塞利还出版了《我牙齿的故事》,这部在形式上大胆实验的小说幽默、轻盈,虚构了许多名人牙齿被拍卖的情景,以去经典化的方式改写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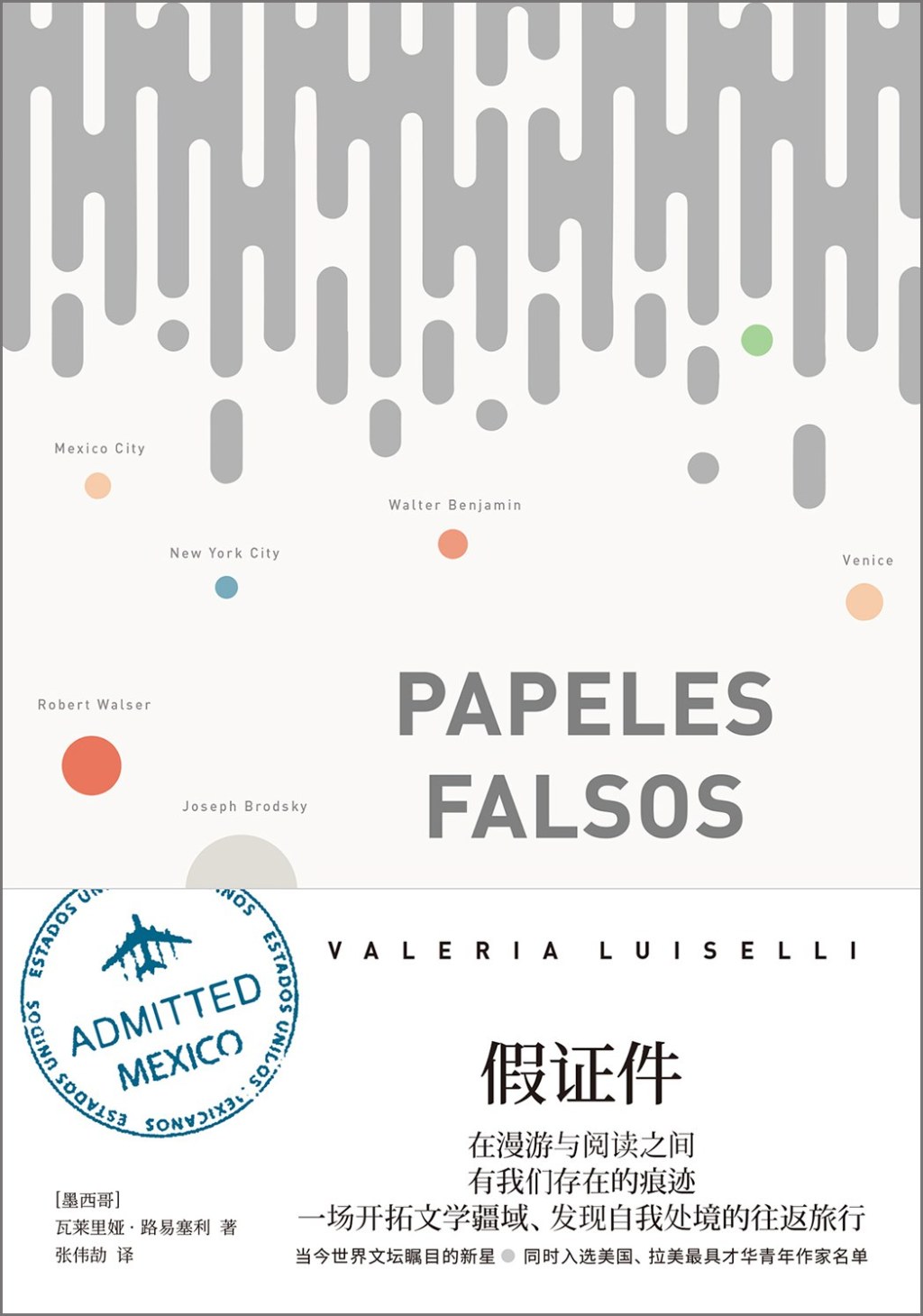
路易塞利著《假证件》

路易塞利著《没有重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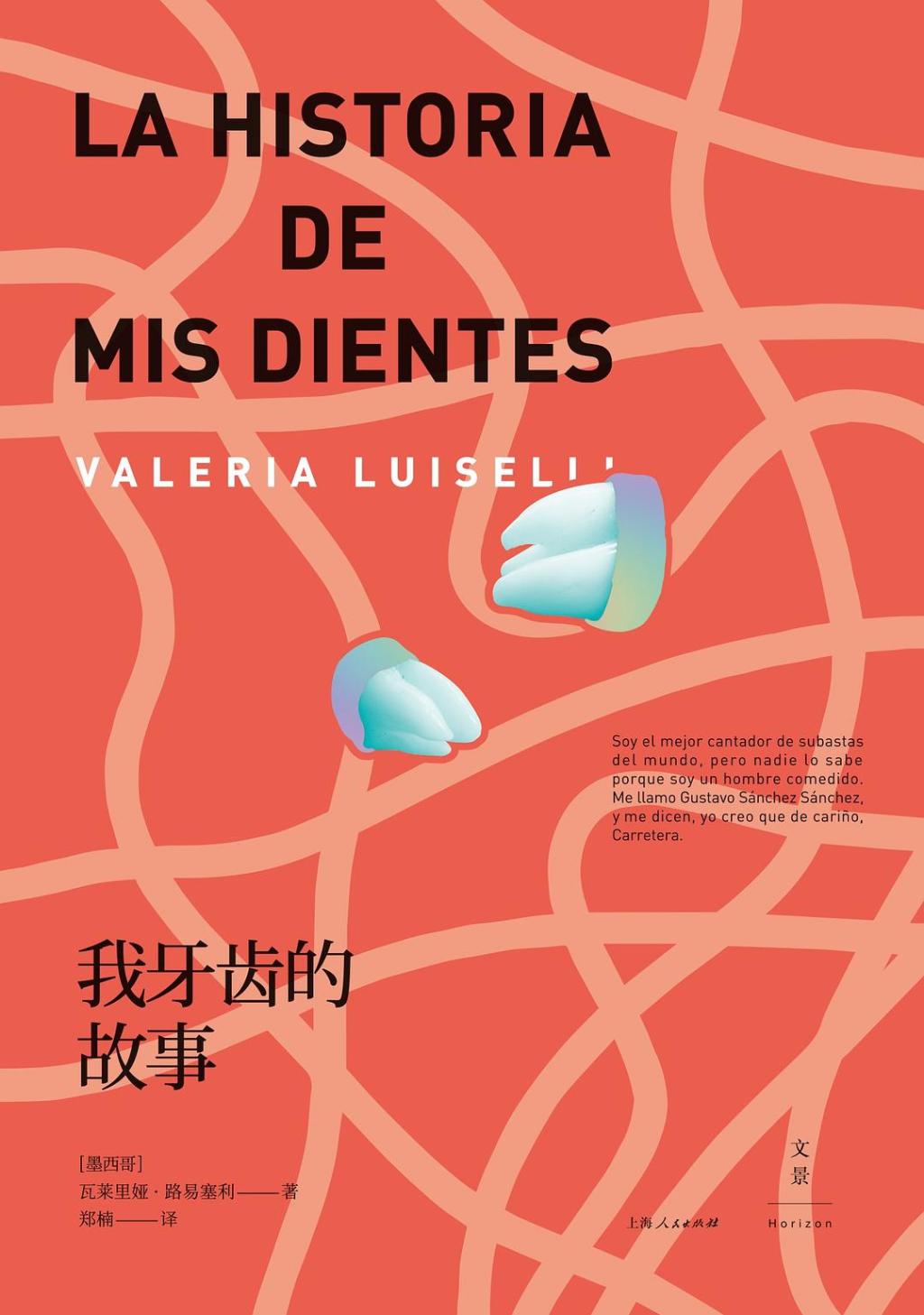
路易塞利著《我牙齿的故事》
相比《没有重量的人》和《我牙齿的故事》,《失踪孩子档案》的篇幅长得多,而且也不像前作那样高度倚赖传记性的素材,其叙事更为完整、连贯和集中。可以说《失踪孩子档案》的出版也映现了路易塞利的写作史,标志着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成熟和野心。
小说最主要的叙事者和主人公是一名从事新闻和声音纪实工作的女性,她因为一个声景研究项目与现在的丈夫结识。两人原本都有自己的孩子,“我”、丈夫、他的儿子和“我”的女儿构成了这个新家庭。“我”偶然认识了来自墨西哥瓦哈卡的移民曼努埃拉,在帮助曼努埃拉把她滞留在美国西南边境拘留中心的两个女儿带回家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制作有关边境儿童危机的声音纪实作品的想法;丈夫则对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阿帕切人发生了兴趣,打算研究这个部族被白人征服的历史,借此复活人们对已被遗忘的某些事实的回忆。于是“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纽约出发,开始了驾车去往美国西南部的旅程。夫妇双方都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他们知道彼此终将在旅途的尽头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一家人也在旅途中讨论着新闻广播报道的难民儿童问题。小说对这个家庭故事的叙述也穿插着作者虚构的一部叫作《失踪儿童挽歌》的小说片段,而《失踪儿童挽歌》的故事显然是指涉现实中来自中美洲的难民乘坐被称为“野兽”(La Bestia)的火车抵达边境的艰险历程。
《失踪孩子档案》借鉴、吸纳了公路小说的叙事元素,具有公路小说的某些特点:情节上比较松散,叙事主要由公路旅行的各个经验片段构成,其中包含充满意外、惊奇的场景,也包含主人公与途中偶遇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叙事人还往往会将自己的人生记忆和眼前不断变化的景观相互对照、融合。但路易塞利也在文体上展现出富于个性的尝试,她将母亲的叙述、儿子的叙述、《失踪儿童挽歌》的叙述以及主人公存放在后备厢的各个存储盒中的档案编织起来,还附上了地图、拍立得照片等图像,展示了由诸多不同材料、媒介构成的丰富的回忆“档案”,拓宽了小说文体的边界。
在斑驳的经验片段之下,小说的核心情节是女主人公内心的成长。然而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经典成长小说模式不同,路易塞利小说中的人物成长并不是到成年或“成熟”/中年阶段结束的,也并不以人物取得某种地位、进入某个阶级、获得婚姻与家庭为结局;这种成长是以女主人公离开核心家庭、对更广阔范围内的政治性议题做出回应、进入政治生活为标志的。凭借展现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努力,路易塞利开拓了一种属于当下的新的成长小说类型。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最为重要的成长小说类型是这样一种类型,其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物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232页)。路易塞利小说中的人物成长也同样反映了历史的变动:近年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受迫害”的政治难民,许多因为本国的贫困、犯罪活动、暴力等问题而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的移民大量涌现,成为既有法律框架还无法完全容纳的新难民;美墨边境难民问题更有其特殊性,它要求跨国主义的理解和治理方式。路易塞利在写作和访谈中多次强调这样的事实:美国政府认为移民危机是别国问题,而并非本国需要积极应对的责任,但实际上这一危机早就变成美国自身问题的一部分。
美国官方对墨西哥工人的招募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很长时间里墨西哥劳动力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期,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反移民的政策;美国本土的毒品消费需求是中美洲向美国贩运毒品的根本原因,这些贩毒组织让中美洲下层民众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刺激了更多合法或非法移民抵达边境;美国介入、资助了1979至1992年萨尔瓦多内战,这场战争造成大量中美洲居民流亡美国,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移民被美国驱逐出境,人员的反复流徙缔结出一个个帮派,甚至形成有军队性质的跨国组织……层层叠叠的因素交织,令美墨边境危机不断加剧。
尽管奥巴马政府的移民政策相对温和,但在奥巴马任期内的2013年,也就是路易塞利动笔写《失踪孩子档案》不久之前,美国仍然大规模遣送了将近两百万名移民。在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著作《移民路上的生与死》中,人类学家杰森·德莱昂揭示了美国边境政策最险恶的、施加系统性暴力的一面:“这群人在迁移路上的可怕遭遇既非偶然,也非愚蠢,而是美国联邦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不仅相当不透明,更很少有人对此直言不讳: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索诺拉沙漠的险恶为掩护和工具的杀人计划。”([美]杰森·德莱昂:《移民路上的生与死:美墨边境人类学实录》,赖盈满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第6页)后来,移民政策在以修墙计划为标志的特朗普时代急剧收缩,特朗普政府一度出台“零容忍”政策造成众多移民儿童与父母被迫分离(不久后终止了该政策)。现在,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墨边境移民的处境很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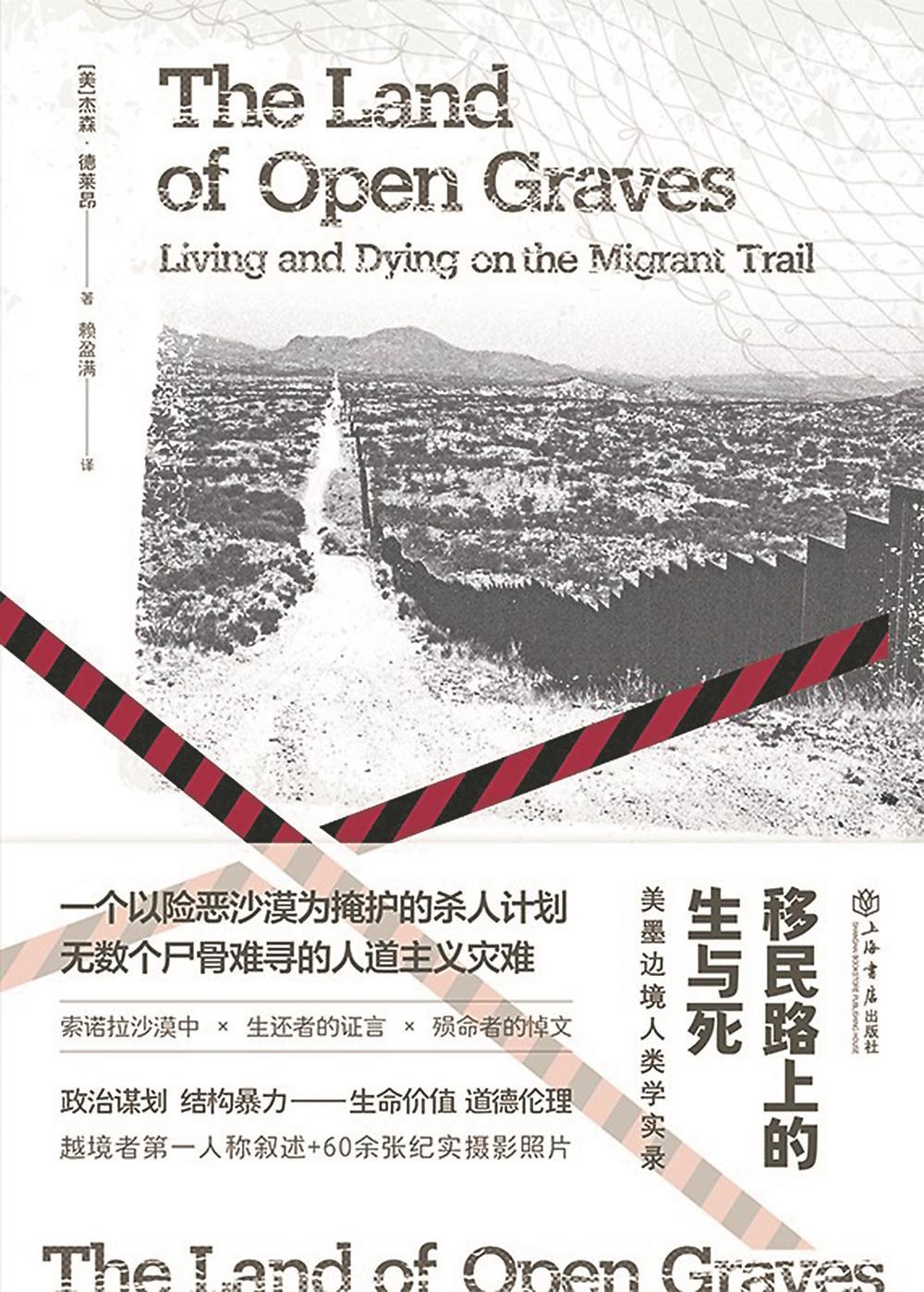
杰森·德莱昂著《移民路上的生与死:美墨边境人类学实录》
相比无证件移民中的成年人,难民儿童经历的人道主义危机更为严重。在小说中,为了方便年幼的孩子记忆,“我”总是使用“失踪儿童”来指称所有的难民儿童,而不仅仅是那些在越境途中失踪的孩子。试图穿越美国西南边境的无人陪伴儿童在二十一世纪不断增多,而在2013年之后,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难民儿童数量已经超过了墨西哥儿童。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在美国有直系亲属,也有一些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许多待在美国的父母听信“郊狼”(即人口走私的组织者)的宣传,相信孩子只要入境就会获得居留权待在自己身边,导致更多未成年人试图入境。而待在美国的父母不能陪伴他们入境,往往是因为这些成年人自己就是无证件移民,出境后很可能无法再次返回。
另一个造成大量移民儿童出现的因素在于,根据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威廉·威尔伯福斯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再授权法》(TVPRA),来自毗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无人陪伴儿童”,除非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者遣返后可能会遭受迫害,否则会被立即遣返,来自非毗邻国家的“无人陪伴儿童”则不会被立即遣返,而是会被转移至难民安置办公室监护,随后一连串冗长的听证程序将会开启,用来审查这些儿童是否符合申请庇护和救济的条件(参考欧阳贞诚:《美墨边境“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特征、缘起与影响》,《美国研究》2023年第一期,68页;阿维娃·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美国持续的边境危机》[America’s Continuing Border Crisis],Guernica网站,2014年8月25日)。因此越来越多中美洲儿童希望充分利用这一规定进入美国。
小说中曼努埃拉的两个女儿属于特例。来自墨西哥的她们本应被就地遣返,但是“警官好心放了行”,随后诉讼开始,但律师为女孩们提交的庇护申请最终被法官驳回。“曼努埃拉得知,她的两个女儿将被人从现在等候处置的新墨西哥州移民拘留中心转移至亚利桑那州的另一所拘留中心,之后将从那里被遣送回国。但是,在被遣送的当天,她们却消失不见了。”小说结尾部分交代,两个女孩最终被人在沙漠里找到。现实中就有许多和小说中曼努埃拉女儿一样的难民儿童,他们在迁徙途中经历了虐待、帮派威胁和严酷的生存条件,最终却也没有抵达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消失和死亡在沙漠里。
正是见证了这种种苦难,女主人公决定脱离作为压抑结构的家庭,重新成为参与公共生活的行动着的主体。她将失踪儿童的处境和自己的孩子反复参照,并通过叙事的行为(在旅途中“我”不断给孩子们讲故事),将他者的故事变成了这个家庭中每个人的内心意识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看到,《失踪孩子档案》在开掘新的叙事领域、发现新的女性行动潜能同时,仍然潜藏着形式上的危机,展现出某种未完成性。一些困惑贯穿着我们的阅读: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作家和艺术家的介入性实践、报道与创作——正如小说叙事者所做的那样——是否真的能影响和改变系统性、结构性的暴力,是否能真的推动这些难民儿童处境的改善?与这一问题相关,小说呈现出一个比较突出的文本征候:对于难民儿童和边境问题这一话题的直接书写,即便加上《失踪儿童挽歌》这一层虚构性文本,在篇幅上也依然明显少于对于主人公个体经验的书写。小说大部分篇幅是在讲述从女主人公在旅途中的体验(当然,这种体验充满了她意识到自己相比那些难民来说更有特权、更受保护之后深刻的自我反思)以及这个家庭渐渐走向解体的过程,还伴随着对种种物理声音的精微描绘。这两个部分尽管有所交叠和互动,但并未有机地融为一体,这种不平衡与裂隙,既显示了文本的多层次性,也显示了作家乃至整个小说文体在面对现实危机时的限度。
从文本上看,女主人公的“介入”方式和她的母亲的介入方式十分不同。小说用几个自然段回溯了“我”的母亲的形象,叙事人旨在借此说明母亲的政治兴趣如何遗传式地影响了“我”的个人选择:“我刚到十岁时,也就是男孩现在的年纪,我的母亲离开了我们——我父亲、我姐姐和我——去加入墨西哥南方的一场游击运动。”母亲的离去让年幼的“我”不解和愤怒,而多年之后与母亲的交谈让“我”开始理解并赞赏母亲当年的举动。对于母亲的解释,小说只给出了寥寥数语:“虽然她很爱父亲,但她跟了他一辈子,总是因此将自己投身的事业搁置一边。如此多年以后,她终有一天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地震’:这地震将其深深惊醒,甚至震碎了她身心的一部分;于是她决定离开,寻找修复这整个破碎状态的办法。”这种政治兴趣和实践既有朝向他者的关切,也有满足自我需求的动力:“震碎”了母亲内心感受的,也许一部分是群众运动召唤出的热情,而另一部分则是多年家庭生活带来的缺失、封闭之感。

路易塞利
根据小说故事和路易塞利本人经历的高度对应性,此处所写的“游击运动”应该就是指实际上路易塞利母亲参与过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1994年初,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生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组织崛起,它以本书中提到过的二十世纪初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命名,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改善印第安农民的生活状况。这场对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主要发生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地印第安农民自治组织不断发展、联合的结果。路易塞利的母亲参与运动的具体方式是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该组织由女性主导,支持萨帕塔运动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妇女和儿童。尽管这场运动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成功,但确实在一定范围内破坏和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对比之下,小说女主人公进行声音纪实项目或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实践固然也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但“我”的意图和手段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我”迫切地关心这些难民儿童并为相关工作放弃了和丈夫的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我”选择的介入方式是通过制作一部声音纪实作品(并写下这部小说)。实际上,这种作品将变成“我”个人成长和成就的一个环节,还面临着被它所批判的整个系统所回收的危险,而这种真诚的自我反思也同样成为了小说中颇为关键和感人的部分。母女之间更为显著的区别在于,母亲的政治实践让她与其他女性个体乃至更多的运动参与者联结在一起,而小说中的“我”似乎只是走出了离开核心家庭的一步,而未能走向更深层的、持续的联结。
当然,在现实中,路易塞利的实践没有止步于小说写作。她从2015年开始在纽约移民法庭担任志愿者,工作内容是为从墨西哥入境的无人陪伴的儿童翻译法庭问出的问题,并把他们的回答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她根据这一经历写下了《告诉我结局是什么》(Tell Me How It Ends:An Essay in 40 Questions)这本小书。也许只有将这部非虚构作品纳入视域,我们对《失踪孩子档案》的理解才算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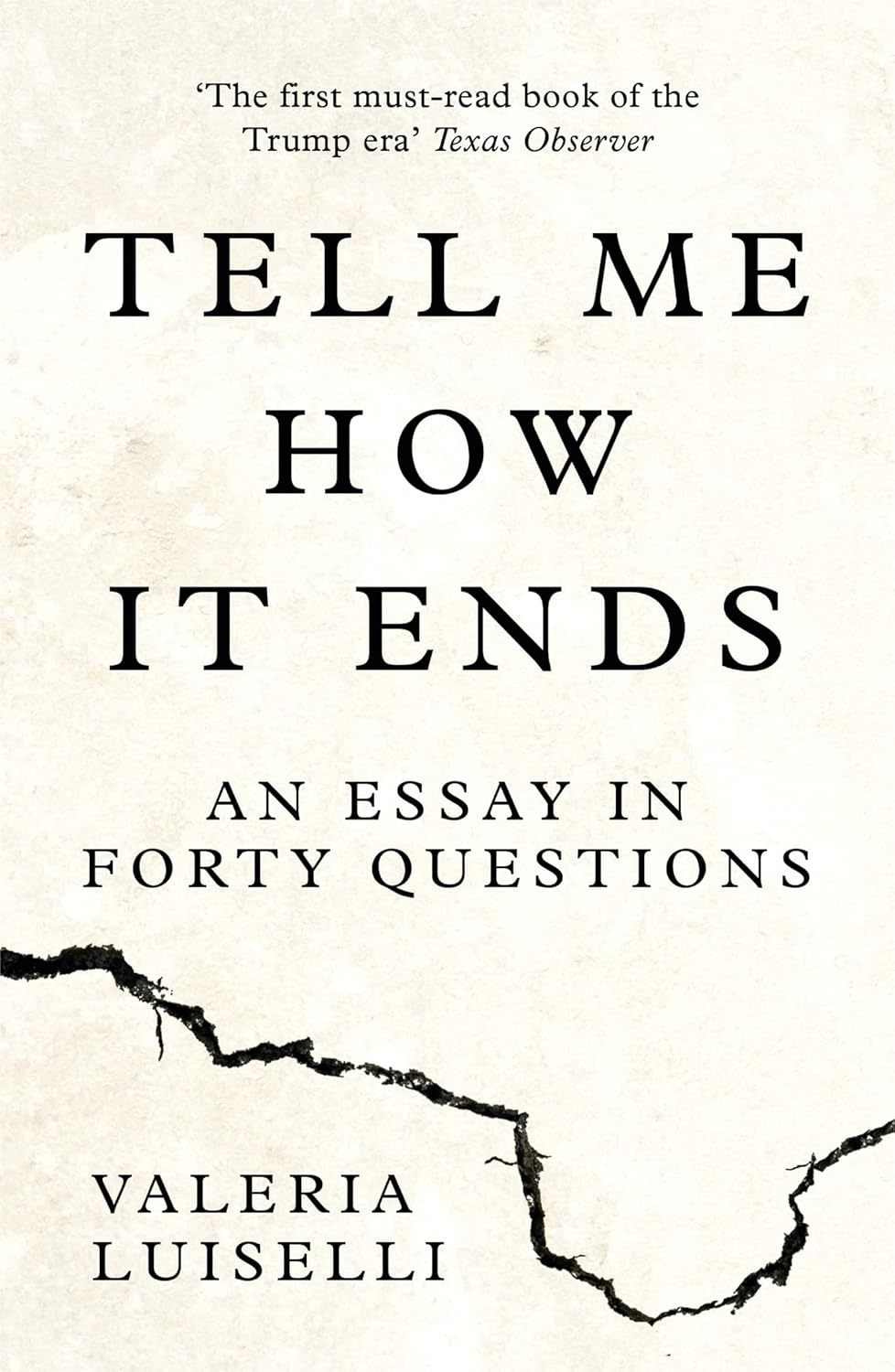
路易塞利著《告诉我结局是什么》
《告诉我结局是什么》逐一分析了路易塞利作为口译员翻译的问卷上的四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你为什么来美国”“你和谁一起来美国”“你在抵达美国途中是否遭遇让你恐惧或受伤的事情”等等),以此为线索讨论了这些移民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小说类似,这本书也将作者自己作为移民的生活体验与她的志愿服务、难民儿童的处境并置在一起叙述,但有关个人体验的内容在篇幅上远远少于对于难民问题的叙述。相比小说,这部非虚构作品针对移民问题做了更全面、深入的展开。作者详细描述了难民乘坐货运列车“野兽”忍受种种恶劣条件甚至承受丧命风险来到美国的旅途,描绘了边境拘留中心里非人道的生存环境,说明了法律规定的难民儿童能够获得庇护或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SIJ)的各类条件——比如要么遭遇父母的虐待、忽视、遗弃,要么是因为种族、信仰、国籍或政治观点而受到迫害;同时作者还探讨了移民危机更深远、纠缠的社会历史原因,讲述了移民来到美国后融入当地社会的具体实践。总体上看,《告诉我结局是什么》不仅提供了更详实的信息,也发出了针对现实状况的更为尖锐的批判,可以看成是一本让人快速了解美墨边境危机的手册。
随着当下日益发展的媒介和密集的信息传播,人类个体对世界的想象能力似乎也随着人类总体认知空白的大幅缩减而萎缩。小说文体,特别是科幻、幻想类小说之外的写实主义小说,越来越多地面临着非虚构写作的“竞争”。当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非虚构写作和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诸多“真实”,有人不禁会问:为何当代人还要读小说?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们可以给出许多强有力的回答——浸满个性与风格的语言本体、对于人物内心和人际关系的深度描绘、重构过去历史记载不足的人与事……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在情节发展的安排中呈现仅仅是非虚构写作所无法承载的有关历史远景的想象。总而言之,小说在与非虚构竞争时需要满足更为严苛、更高层次的要求。
以这样的标尺来看,我们会发现,尽管《失踪孩子档案》在讲述他者的经验时比《告诉我结局是什么》显得更为抽象、浅表,比如曼努埃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始终作为次要人物甚至背景声音而存在;但它在描绘叙事人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时,仍然突出体现了上述大部分小说本体特征。
如哲学家玛莎·C. 努斯鲍姆所言,小说和文学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够激发公众的积极情感,从而有可能促使人们投入正义的政治行动。在努斯鲍姆看来,任何一种同情的政治运用,都需要创造出稳定的而非短暂的、偶发的关切。“如果远方的人们与抽象的原则要支配我们的情感,那么这些情感就必须因此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置于我们的关注圈内,造成一种属于‘我们的’生活的感觉。”([美]玛莎·C. 努斯鲍姆:《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陈燕、卢俊豪、李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14、209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失踪孩子档案》的主要意图不是像非虚构作品那样提供经验性信息,而是书写同情如何发生,又如何绵长而深刻地改变了更受保护、更有特权的那些人的生活,把原本属于他者的问题变成了“我们的”问题。它描绘了一个母亲和创作者如何从自己的经验、身边的世界出发,想象和理解那些失踪儿童的命运,而将主人公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危机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她在收集这些失踪儿童故事并将之讲述出来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恐惧、愤怒、同情和爱等等强烈的情感。

努斯鲍姆著《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
路易塞利的叙事以细腻、感性的女性声音进入政治生活,为原本由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提供了生动且必要的情感维度,她的小说和非虚构写作不仅展现了女性写作的独特价值,也又一次突出了情感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还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家庭的属性:母亲、妻子的身份并不应该与女性的社会责任相互冲突,至少我们应该为此努力;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也不仅仅来自亲情与抚养,而在于共同面对社会的困境和危机并从中学习,在彼此的激励中持续地自我教育和成长。不过,如果要弥合小说中两种叙事内容之间的裂隙,让小说主人公和那些历经苦难的人们形成更持久、深层的联结,这就不仅仅是小说和文学内部的问题——或许《失踪孩子档案》在形式上的危机,恰恰召唤和预示着新的历史意识的萌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