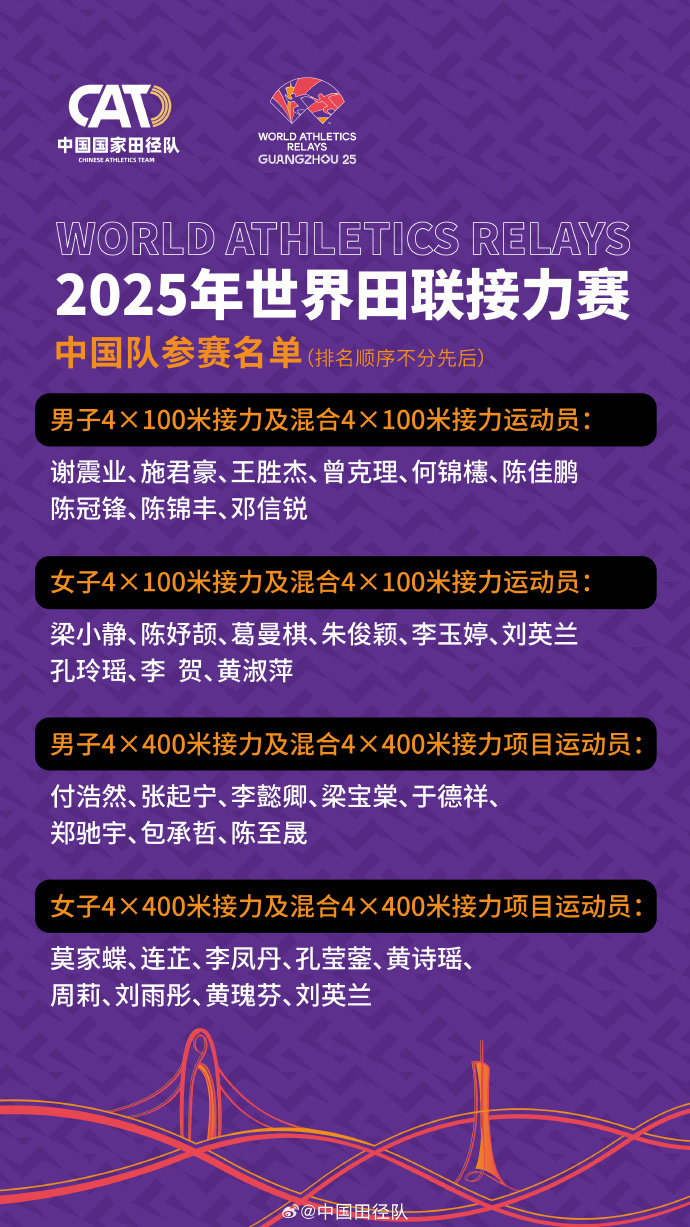露西哈特菲利亚:一个免费看片高清在线-讲座|现代女性在面对生育、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复杂抉择
前不久,作家毛利携其最新力作、长篇小说《生女有所归》在杭州的纯真年代书吧举办了首场读者见面会及新书分享会。

毛利,作家、自媒体人,电视剧《小夫妻》原著作者,已出版《全职爸爸》《结婚练习生》《我在三十岁的第一年》等多部作品。她所主理的微信公众号“和毛利午餐”成为情感、家庭领域头部公众号之一。
在这次分享会上,毛利与金话筒得主、浙江FM93交通之声资深主播孙婧以及到场的读者们深入讨论了《生女有所归》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主题——现代女性在面对生育、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复杂抉择。书中通过两位女主角——文敏和缪琪——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女性如何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压力之间寻找自我定位,并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除了对书籍内容的深度剖析外,本次分享会还设置了互动环节,让现场读者有机会直接向毛利提问。从创作灵感来源到个人生活经历,再到如何平衡写作与育儿之间的关系,毛利都给予了真诚而深刻的回答。特别是关于“全职爸爸”现象及其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看法,引发了在场家长们的强烈共鸣。
以下为分享会部分内容整理。

讲座现场
孙婧:今天大家拿到的这本书,应该是带着新鲜的还有印刷机温度来到大家面前的。这是毛利老师这本书出了以后第一次的分享会,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看过。我比较早前两天就已经拿到这本书了,确实这个话题很及时。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你也是。每一个女性几乎都要面对一个家庭事业,还有一个自我的问题,在三者之间不断地去博弈或者平衡,但其实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做出了一些选择。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是不后悔的,我们对生育这件事情充满了感恩,收获了很多,但是当你回过头去想,如果这一切,尤其在养育一个孩子的过程里,你要去重估价值的话,那么毛利老师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角度和切入点。书里面有两个不算典型的主角,文敏和缪琪。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主角和她们的故事,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观念问题。
毛利:其实刚才你说作为母亲大家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是到第二胎才不后悔的。我第一胎的时候一直很后悔,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从头到尾什么事儿都难,吃喝拉撒没有一件不难的。一胎确实可能是我第一次面临这种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
孙婧: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本书的名字“生女有所归”的时候,就想起来我家老大是女儿,我两个都是女儿,所以你不会有我这种感觉。你老大是儿子对吧?人家说生儿子的话都可以叫做“英雄母亲”,男孩小时候妈妈要更辛苦一些。
今天第一个话题,在婚姻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权力的味道,比如说你我都面对过生完孩子以后的艰难或者是反思我后不后悔,但男的就不会,或者男的更少一些。在书里,有一个丈夫的角色——小宋,他是在家庭主夫这样一个角色里面遇到了一些身份转换的问题。所以男女在婚姻里,面对生育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权力表达吗?
毛利:我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人物?这本书里面其实是双女主,原来设置的第一女主角就是文敏。文敏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业上的大女性,30岁之前已经赚了很多钱,通过开教培机构收到了第一桶金,然后赚得挺多的。但是因为当时这本书的节点正好是我们国家有政策出来,所以她的事业一下子就停滞了。书里面就讲到,你现在终于空下来了,不是正好去生个小孩吗?一个女的不能搞事业了,还能生孩子呀!但是对她来说有一个很为难的点,她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她要确保如果我生小孩的话,我的老公就是一个贤内助,而不是说我来做贤妻良母的角色。当她不能确定这件事的时候,她就进入了生育的犹豫期。当她的事业停滞的时候,她老公的事业正好起飞了,然后她会觉得,难道我现在就要重新回到传统女性的赛道了吗?其实这种行业的变革可能对现在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会焦虑的问题。比如说我也会焦虑,我之前可能自媒体的收入占大部分,但是从2023年开始,自媒体这一块就不太好了。我丈夫开始卖花生了,你会有一点焦虑,如果他变成我们家的赚钱人——当然我觉得在任何权力关系中都是一样的,肯定是赚钱多的那个人是占据权力地位的,就是他是家里面的话事人——我能不能接受这种角色上的错位。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会非常代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如果我要开始当他背后的女人,我能忍得了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事业型女性的焦虑。
孙婧:我焦虑倒不至于,但是你说的感觉我懂,我们似乎把它设定成了一种此消彼长。大家会在观念里有这样一种定律,要么你赚钱,要么你养育孩子,但事实上婚姻里面,我们结婚,然后一直到老了,孩子长大了,不是大家都干了这件事吗?生存,养孩子?
毛利:可能在很多家庭里面,夫妻还是会有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特别是在钱这个问题上,突然一下子一个人的收入变得突飞猛进的时候,肯定他自己会有一些很典型的反应。比如说书里面有一个让文敏感到惊讶的情节,她以前都是一回家老公给做饭,弄得好好的,当她事业停滞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加班回来,进门第一件事就说“我都不能有一碗面条吃吗”,类似于《再见爱人》里面麦麦说“我不配一杯咖啡吗”,他会特别忍不下这口气。就是你没有说我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家庭里的定位就是我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她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孙婧:在家庭这样的一个小的团体组织里边,不像在工作上很清晰,有层级,有分工,这种权力之争,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夫妻俩,我爸妈偶尔过来一下的话,今天晚上吃大白菜还是小白菜,这个事也决定了到底谁说了算。在日常里面我们可能会没有想过它确实是个问题,但当它和生育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权利就显现出来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家庭关系里面,就夫妻之间来说,再往下一步就要选择生育了。我好像没有(选择),就自然而然的,时机合适,又没有不要的理由。
毛利:这就是时代的差异。现在已经没有意外怀孕,所有的人都是从备孕开始,是一个非常久、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在996,如果你要备孕就意味着你的身体要先调理好。我对90后的调研,身边好像所有的人在生育之前都会经历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备孕期,而不是像我们这样说有了那就生。
孙婧:所以这是一个进步吗?还是某种对我当下的不自信?比如说我们过去生孩子自然就有了,是不是默认我每时每刻身体都是健康的和适合生育的?但今天的年轻人要经过一个选择,是不是意味着我当下的生活质量没有那么的让我自信,我得专门为这个事情来调理一下土壤,然后再进入这个过程?
毛利:其实大家都对自己的健康有一种恐慌。

《生女有所归》,毛利/著,湖南文艺出版社·灯塔ALight,2025年2月版
孙婧:书里面的话,其实展现了很多女性自我实现的困境,尤其是缪琪在离婚以后选择接受相亲,还有社会对离异女性的偏见,至今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女性离异了,或者女性自主选择不生育,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今天的社会大家不是已经价值非常多元了吗?我们是不是仍然生活在这样一种压力中?
毛利:我书里面每一个情节都不是我脑袋一想说出来的,小区里有几个人在说离婚妇女的坏话,我真的听到了。我昨天还在跟我的编辑老师说,看到书里面有一句话,最好的作家都是谎言高手,非常善于编织谎言,我属于没有办法捏造情节的。实际上,比如说像现在上海这么开放的大城市,可能作为一个离异妇女是很OK的。但是我把她放在松江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亲朋好友的熟人圈,离异或者未婚生育这些事情,在熟人圈里面是很容易被人嚼舌根的,会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这事有一些评判。
那些说你的人根本也不在乎你,他就是为了想显示自己过得好。这种八卦和坏话的来源,就是我们去寻找这些人嚼舌根的根源,肯定是为了体现“你看我过得很好,我没有离过婚,我正常生育了”。
孙婧: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这样一种所谓的价值正确的时候,仍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在。而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在其他渠道的探讨当中,会认为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这个认知是有错位的吗?就你以为有更多的选择了,但其实还有一个标准答案在那里等着你?
毛利:舆论就是这样的,说八卦的人永远都在,不管哪个世界他都在,不会因为世界的进步,这些人就通通消失了。这些人并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用去在乎这些人,他们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孙婧: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判,始终还是有一个单一标准在的,但是我们内心要知道,我并不是因为被归为了某一类、是某一个性别或者某一个年龄层,又或者是我生过孩子、没有生过孩子,而给自己设定一个圈。这点是挺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对婚育是一种权利的反思。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细节,也和现代女性生活里的一些琐碎场景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些琐碎的场景我觉得其实特别的扎心,它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一瞬间觉得原来生活的真相是这样,比如说有外卖80块钱的沙拉。
毛利:我在上海经常点。我其实每次点都在想,这个东西好像不值得我付出80块。
孙婧:然后当我们不点80块钱的沙拉的时候,意味着我要花时间去做一份沙拉,这个事情我要评判一下它的价值。
毛利:后来随着我自媒体收入的下降,我确实不点了,我现在每天在家就吃我爸做的家常菜。
孙婧:一下子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相亲市场的男性多样化,这个话题该怎么解释?什么叫男性的多样化,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
毛利: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了解现在的相亲市场,去相亲前觉得“我累了,我想找个男人好好过家庭生活”,然后你相完亲之后想的是“我还是得好好上班好好干,谈恋爱不如搞钱”,这是现在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你赞同吗?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对象,实际上那些值得依靠的对象是不流入相亲市场的。
孙婧:我先生是我相来的……
毛利:那可能是你那个时代的事儿,现在这个时代,正常的交往对象似乎都不会流入市场,不管是相亲还是约会软件什么的。
孙婧:但是今天年轻人走向婚姻、走向生育的过程之难,我也有切身感受,有人说是因为生活压力,完全是压力还是观念的转变?
毛利:现在两极分化很明显,有一个划分是现在还愿意结婚的女人是传统女性,所以彩礼会提得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人没想明白,还有一些人就彻底想明白了,就不想结婚。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市面上90%的人在看剩下10%的人谈恋爱,然后这10%谈恋爱的人,比如说各种分手、换男朋友频率很高,但是市场永远在这10%里面流动,剩下的90%都是出门都觉得好累,算了不去了,就在家里挺好的。
孙婧:这个比例,我其实是有点震惊的,因为我原来没想过会相差这么大,我以为一半一半,但是居然看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谈的人变成了少数。
毛利:因为谈的人次数多,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市面上还有很多情感故事,但实际上很少。目前我还在写一个情感专栏,我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到写情感专栏,我的助理,他是1994年的,还有我认识的什么1991年或者1997年、1998年的,统统去问一遍最近身边有什么情感故事?有一次,我助理就告诉了我好几个,我说为什么这次你认识得这么多?她说因为我跟一个朋友吃了饭,就那一个人的。
孙婧:我现在在高校里也会上课,校园应该是最容易谈恋爱的地方,但是我会发现大学生这个群体,他们的恋爱也乏善可陈。
毛利:因为他们会把约会当成是面试,很累,不想去被人评分,也不想去评别人的分。
孙婧:我们在重估这件事情的价值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女儿进入青春期了,在面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要跟她讲其实恋爱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和当下的社会现象就会有一种错位,你看那些人都在这么说,而我要告诉你是这样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应该告诉她其实婚姻是一个经济合作体的选择,还是说婚姻就应该是爱情自然而然的产物,它应该和爱情有着极强的关系,而不是应该去做各种利益考量。我其实有点疑惑了,话语权到底该偏重于哪里?
毛利:我女儿还小,还没想到这个事儿。我其实觉得结婚这件事儿确实会变得越来越少,这是不可挽回的一个事情,甚至可能也不是个坏事,就是一件东西他在消亡之前被讨论的次数是最多的,大家都在想这个东西还要不要,所以很多人开始讨论它。包括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后悔,因为去年我出《二胎记》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这个名字让我不敢往家里买。这本书原来连载的时候名字叫“卵子的呐喊”,又有点太直白了,我就把它改成了杜甫的一句诗,“生女有所归”,又有人看到封面上印着“生育是一个选择题”,我想糟糕了,应该上面印“上海郊区爱情故事”会比较好卖。
孙婧:所以你在给这本书选主题的时候,最初其实谈的也是生育的选择权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这样直白地把它表现出来的话,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毛利:其实生育这个事儿,光看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很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会不想去触碰这个事儿。这本书一开始是我在公众号连载的,连载的时候本来第一女主就是文敏,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事业型的女性,有很多事业型女性的焦虑。但是写着我发现其实大家更关心第二个女主缪琪,因为缪琪离婚了,然后她有两个选项,这种情感的拉扯大家看得很起劲。对于婚姻中的故事,大家就会兴趣减弱,因为婚姻中大抵都是鸡毛蒜皮,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对于缪琪来说,是选年轻的男友还是选有钱的前夫,大家都会觉得有兴趣看。
孙婧:当代入自己的时候,发现好像婚姻里还有另一道选择题。其实我们探讨婚姻、家庭、女性成长等这些社会话题,会发现它永远是媒体上热议的话题,也是在自媒体当中被讨论最多的,可以说看到很多的女性博主几乎没有能够避免去谈到女性的立场,包括女性选择的,基本上都会做一些自我的表白和剖析,并且大家在表白和剖析的时候都要仔细地去想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子。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初的创作动机和你做自媒体的一些判断会有关联吗?你会考虑当下人们真正喜欢的女性立场是什么吗?
毛利:因为我自己也稍微有一个小小的规划。我从30岁的时候开始写长篇小说,《我在三十岁的第一年》是讲恋爱的,然后到第二本《结婚练习生》是讲结婚的,第三本就会写生育题材,然后今年接下来连载的一本可能就是讲离婚这种题材的。
我为什么想写生育这个话题?是因为以前的小说我们在写到女主结婚了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她的故事还没有完,因为她还可能会离婚,但是写到女主怀孕了,肯定后面没有了,不然还能怎么样,肯定就跟孩子他爹过呗,不管怎么凑合,对不对?但其实,这本书里面的两个故事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说缪琪,因为她前夫不育,两个人离婚了,后面又怀孕了之后,前夫去找她说要不我们就还在一起。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当时也是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会觉得原来你就算生育了,就算怀上了,你其实还是有得选的,因为现在单亲生育也不会觉得是一件非常耸人听闻的事。
孙婧:这两个女主角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个?文敏和缪琪她们两个哪一个是你生活里面会真心喜爱愿意和她经常在一块的?
毛利:我都无所谓。可能一开始我会带入文敏更多一点,但其实我的底色是像缪琪那样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成长起来的普通女孩。她是独生女,之前有一个读者留言说这本书里好像前半部分关于重男轻女的故事,他看得很有触动,但是重男轻女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文敏她作为一个有弟弟的女孩,虽然算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她会比缪琪来得更激进,因为她从小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起来的,她要摆脱重男轻女这个事儿的话,需要付出比缪琪更大的努力。比如说,缪琪肯定她爸不愿意给她钱,跟他闹翻了,就不跟他见面,其实她的内心会有一种底气,反正将来都是我的,现在闹翻就闹翻。但是文敏她可能是闹翻之前要告诉她爸,你给我弟弟多少我也一定要多少,不然我就不跟你相认。她会在重男轻女上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我觉得跟独生女还是很有区别的。
孙婧:而且现在大家会发现对于像文敏这样处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我最近看到一个帖子,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独生女就没有被重男轻女的观念所影响,比如说人们会说你生个女儿有福气,说你妈妈后来买了很好的房子,把钱会更多地用于享受生活,因为她生的是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女,大家会认为,其实这也是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觉得这样想的话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生一个儿子,有给他买房子、娶媳妇的义务这件事情,并没有说就压迫女孩。你会觉得一部分人去做有没有被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伤害的反思,是必要的吗?
毛利:可能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会出现。缪琪是上海郊区的独生女,她会不太理解为什么文敏会用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因为她没有在她的处境里面,就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在文敏的处境里面,她如果不做得那么绝的话,她的人生就可能会走向“扶弟魔”那条路。
孙婧:书里面的话,两个主角,文敏和缪琪,她们性格设定都很鲜明,包括在事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上,也包括遇到的一些际遇的问题,你刚刚说是有原型的?
毛利:每次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开始先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会一直把它放在大脑里面,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想一想,就好像它是一个大纲一样,但是不能直接说我就按照这个人来写。我会开始慢慢地给它填充,大概在写作之前做30%提前的预想,开始写起来的时候,其实人物有自己的走向。
孙婧:当你说80块钱的沙拉,其实你是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带入进去了,其他关于那些婚姻和生育上的现实选择困境的话,你有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某一个瞬间的感受带入进去吗?
毛利:就是焦虑万一要去伺候老公怎么办。
孙婧:这其实是你的经历吧?
毛利:我之前写《全职爸爸》的时候,可能是媒体收入特别好的时候,所以就不会有焦虑,那个时候只会觉得肯定会一路这样下去。等到后面慢慢会去想这个事儿,其实就会发现你离传统不是很远,你离传统的生活并不是说已经遥不可及了,而是你如果稍微退后一点点,那些传统的东西就会又跳出来。比如说有时候我去福建,小陈的发小一起喝酒,他们就会觉得喝酒这个事儿必须得喝,不能不喝,所以我会在书里面设置一个情节,一群男的喝得烂醉,然后文敏在那边一拍凳子,说老娘赚了几百万,没有一毛钱是喝来的。会有这样一种内心的声音,但是实际上你离这种传统大男子的权力结构并不遥远。
孙婧:所以,在我们生活里的各种选择上,包括饭局也好,其他的社交场合也好,会遇到男女权利又回到传统的状态,我们需要时时警惕吗?
毛利:反正我时时警惕。
我一开始设置文敏是那么一个嚣张的人,为啥?因为我会觉得她之前真的靠教培赚了很多钱。我之前碰到过一些比较传统的女性,其实是家里面赚钱的主力,但是她为了让先生觉得面子还在,一回家就会变成是在权利下面的,我就觉得,你都已经是这个位置了,还要去讨好这个人。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吃惊,所以我就把文敏这个人写得更嚣张一点。
孙婧:最后希望你来谈一下,就是这本书含了很多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期待,包括对生育观念的一些思考,你核心想传递的思考是什么?
毛利:其实每一件事情,一个人不管做出什么样的抉择,都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当我们置于具体的处境中的时候,比如说这里面的缪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需要钱的人,也不需要过什么奢华生活,现在的日子就很好,但是她会碰到需要一大笔钱的状况,然后到这种时候,其实她的人生选择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好像大女主所向披靡,但其实每一步都没有那么简单。

讲座现场
Q&A
Q:我之前看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好像每天都在写公众号,但是你说写长篇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你现在的写作是那种工作的责任感在驱使你写,还是你写的过程其实也蛮快乐的?你怎么坚持一直写?
A:我其实是一个极度内耗、极度焦虑的人,我如果不写的话,就得去挂精神科,而且公众号是短效的,它只能解决我暂时的焦虑。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坚持写小说?有一次谈过,是因为现在随着我的公众号越来越多人看,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她的故事,说完之后就会说,你千万别写我,千万不要在哪提我,我就会愣在那,就会想,你告诉我干嘛。这个事让我很难受。我真的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有很多其实很炸裂的故事,但是我不能写在公众号或者微博上,这就促使我要把它全都写到小说里。
Q:毛利老师你好,我是2018年才开始正式关注你的公众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生了二胎,考虑到家里没有人养育二胎,没有更多人介入这个事情,我老公就从大厂辞职,我从国企辞职。刚好关注你的公众号,然后看你的文章就讲那时候小陈也是开始做全职爸爸,我就觉得你们家情况跟我们家好像。我想问的是,小陈可以一直做全职,我老公后来又步入职场,但是他的职场规划是受到一定影响的,我觉得作为全职爸爸,这个职业很不错,但是后期的他们怎么办?他们值得去做全职吗?
A:我们陆续碰到这样的问题,但好像全职妈妈的丈夫不会有这种“我老婆牺牲了这么多,我应该怎么样为她准备好后路”的想法,反而是有全职爸爸的都在拼命讲后路这个问题。2023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让小陈读个书,镀一层金,结果去了之后他一直不肯念书。这个事情你为他想得好好的,跟鸡娃一模一样,让他先去考个雅思,然后再去申请一个硕士,也没有想到让他去读MBA,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去读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因为他做育儿博主不能光做那种吐槽博主,有点技术含量,能够带点心理思考什么的,肯定对他带娃也有帮助。然后有一天,他忽然坦言跟我说,他不喜欢学习。这种事情你是想不到的。你已经40岁了,不想再背英语单词,我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我觉得,也可能是男性跟女性的差别,男性会觉得有些事儿可以先推一推。所以,现在我们家有三个不爱上学的人。其实也不用为他们考虑太多,船到桥头自然直。
Q:毛利老师的公众号我是经常翻阅的,很多读者都在问你关于输出的问题,因为你是二宝的妈妈,我就有一个疑惑是关于输入。很多人的输入是靠不停地看书或者看剧,然后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你的生活被家庭捆绑得有点紧,你主要有哪几种输入的方式?第二个问题,你主要的写作路线都是通俗故事,有没有一点担心经常在通俗这条道路上,最终会陷入一些家长里短?
A:首先第一个关于输入的问题,我其实还不算是过得很好的人,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比如说最常见的痛苦就是,带两个小孩去旅行,他们在不停地挑战我这种痛苦。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部分,你想我这个年纪,目前家庭稳定,也不可能换个人去体验,我只能去体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点给我的冲击。还有一部分是靠看书,看看别人的想法,然后跟别人碰撞一下。第三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感悟越来越多,完全忍不住,好像以前很多问题是这么思考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会完全换一种角度,对照来看,觉得怎么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微博仅半年可见,因为我觉得如果前面的翻出来看,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分裂,但实际上你确实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Q:这是你快要步入40岁带来的裂变,还是其他原因的反思?
A:我反正日常总是想想这想想那,随时都在反思中。
还有关于通俗小说会不会变得家长里短,确实会。比如说我最近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是我在写一个新的小说,叫“三个女性的婚姻生活”,她们选择了三条不同的婚姻之路,但实际上婚姻这个东西你写起来,光靠狗血情节来填充会不真实。如果都是狗血的话,你的婚姻不可能持续那么久。但是当你鸡毛蒜皮写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也觉得写得没劲。通俗小说其实还是暧昧的拉扯最好看,但实际上你跳入婚姻之后会觉得要写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挺难的。努力努力吧,写出来之后看看大家的意见。韩剧其实也在进步,可能反转很多,现在短剧也是一上来各种各样的反转。我最近看一个英剧叫《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就四集,讲一个男主播陷入丑闻。这个剧其实看得很累,因为每一个场景都会反转,但是我不可能去写这种反转很多的故事。我活到40岁,就挺想写婚姻这个题材的,不然结婚这么多年不是浪费了吗?市面上很多人写婚姻的题材,这些人未必结过婚,我好歹结过,还结了这么久,我觉得我是应该写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