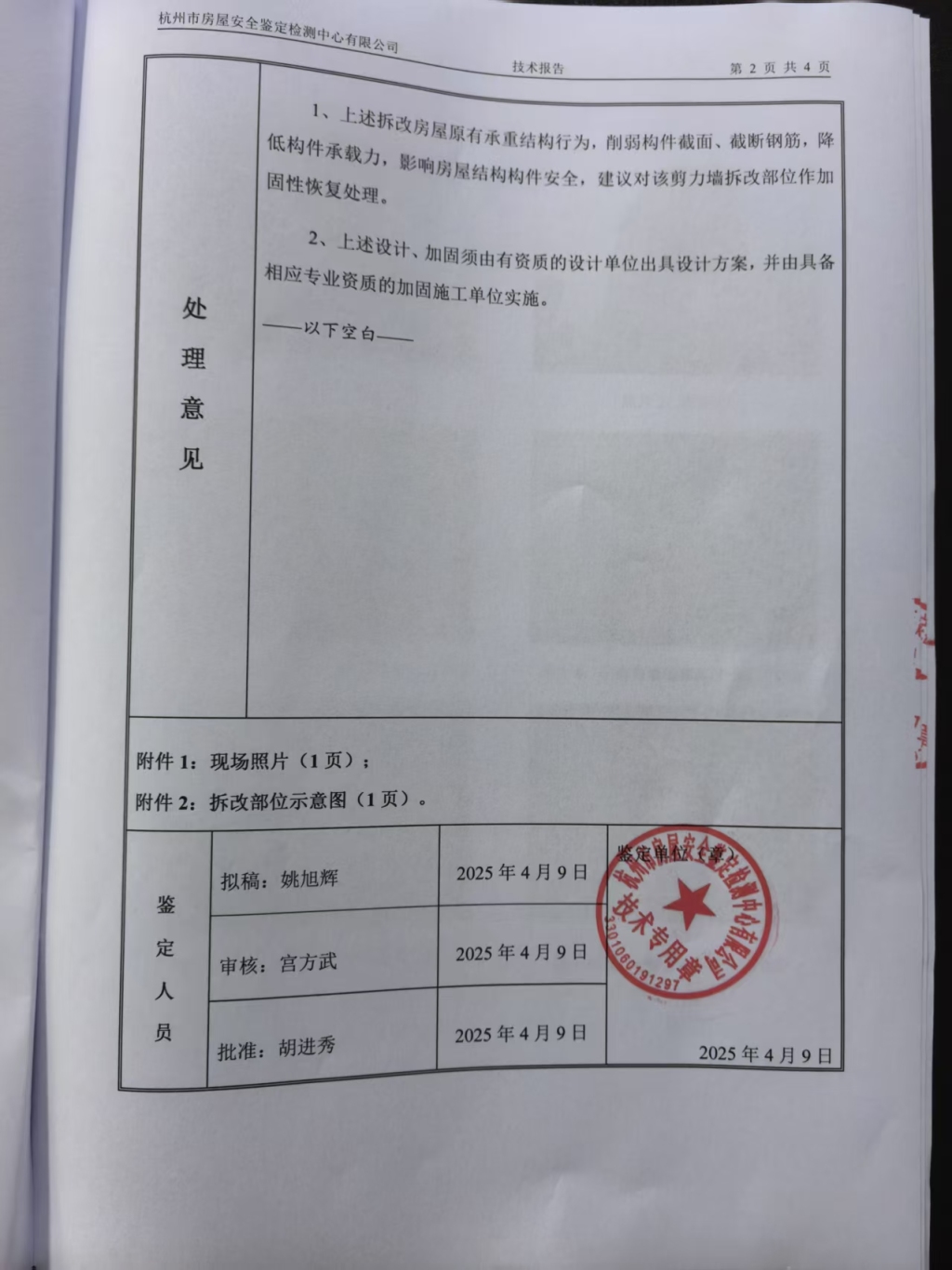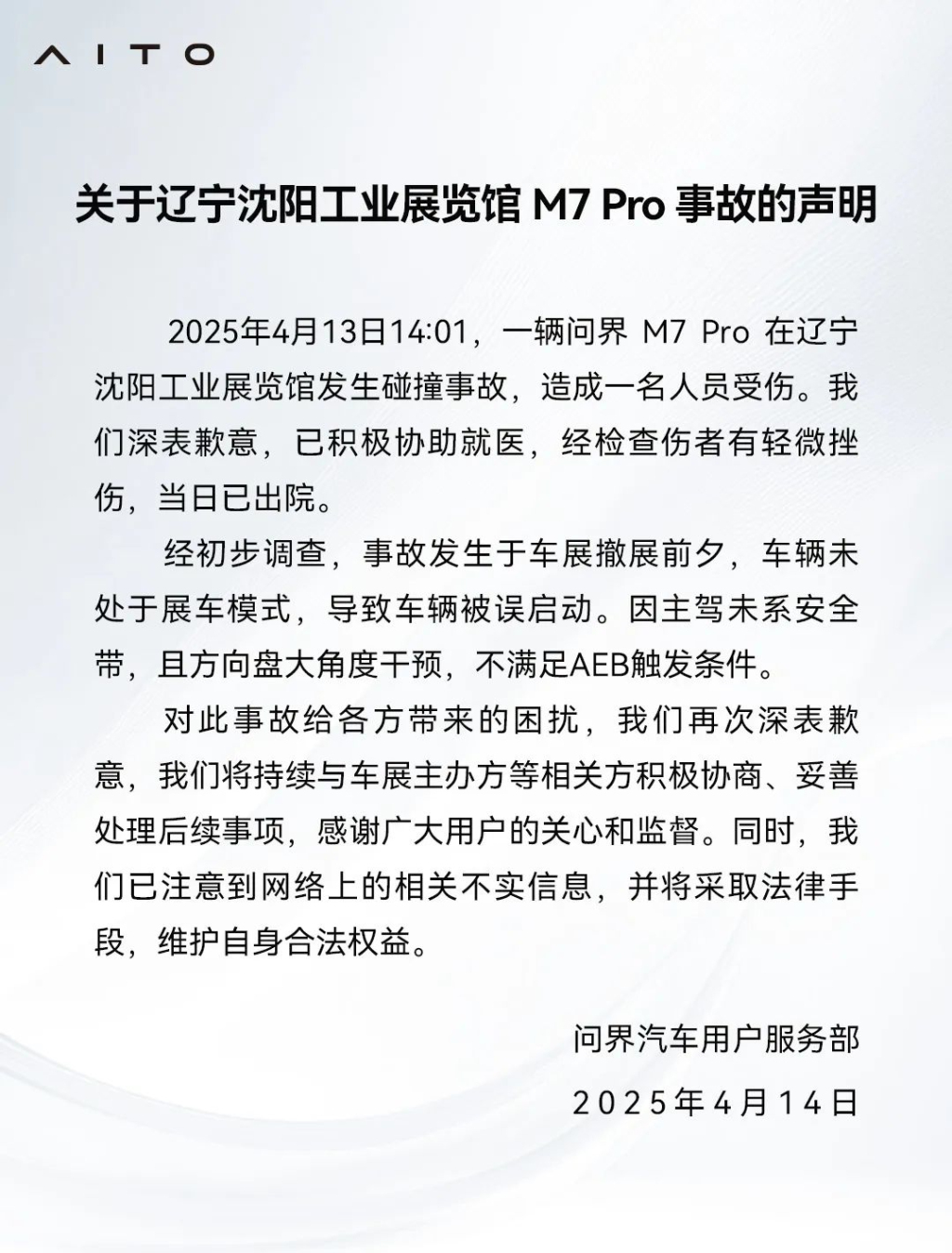十8禁用B站在线看漫画:扒开白沉香白嫩的小屁股-澎湃思想周报|马斯克与美国政治的梗图化;消失的女性自闭症患者
马斯克将玩梗引入美国政治/政治的梗图化

2025年4月10日,埃隆·马斯克在白宫。
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高调担任美国“DOGE”(政府效率部,一个临时机构,主要任务包括削减联邦开支、审查政府合同和项目、裁减冗余人员等,引发了广泛争议和法律挑战)非官方负责人、发起多项政治行动(包括最近为威斯康星州一位保守派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造势),数月来深陷舆论泥淖。
马斯克究竟何时、如何退出尚不明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留下的影响远远超出他所发起的DOGE组织的破坏性行为。通过其线上线下的表现,马斯克将一些原本局限在网络边缘的极端、有毒、玩世不恭的政治观念,成功引入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中枢。
贝鲁特作家Ayman Makarem不久前在半岛电视台网站评论了马斯克如何帮助了那些长期潜伏在网络边缘的有毒与玩世不恭的政治观点进入主流。
比如,2025年1月20日,在特朗普就职后的某场活动中,马斯克疑似做出纳粹敬礼的举动。他随即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这一指控,用否认和玩笑混合的方式发布了一系列与纳粹有关的“幽默”内容。
这正是典型的“钓鱼”(trolling)行为——在网络边缘社群中十分流行的手段,在这些社群中,有毒与虚无主义的政治观点早已根深蒂固。4chan,就是这些社群中最臭名昭著的网站之一,而据说马斯克本身就是其常客。今年年初,他甚至将自己的X账号名改为“Kekius Maximus”(网络梗图文化中的一个讽刺性术语,源于“kek”这一符号,最初“kek”作为网络笑声的变体在《魔兽世界》中诞生,后来被极右翼网民文化所采纳,代表一种“神圣的混乱力量”或“meme魔法”,通过网络平台如4chan等传播,并与古埃及青蛙神Kek相关联,逐渐演变为一种模仿古罗马的讽刺性标题,因此“Kekius Maximus”可以理解为“至高无上的Kek”,或“终极meme皇帝”,它既可以作为右翼群体自己用来调侃和象征自我认同的术语,也可以被外界用来讽刺和批评这些右翼文化现象),头像换成了“佩佩蛙”图像——这些梗都直接来源于4chan。马斯克还在X上公开提到过4chan。
尽管许多人听说过4chan这个名字,但大众对它是什么、以及它与美国极右翼崛起的关系,仍然知之甚少。简而言之,4chan是一个无需注册即可匿名发布文字和图片的论坛。自2003年创办以来,它逐渐形成一个以讨论、恶搞与“社群文化”闻名的网络空间。2010年,该网站月访问量为820万,到2021年已达2200万。
正因其匿名性,用户敢于表达各种问题性观点,常以玩笑和讽刺的方式呈现。这种充满反讽与虚无感的表达风格,逐渐成为4chan的标志。在这里,你常能看到带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言论的“笑话”。而任何认真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反而会被群嘲为“太天真”或“过于正经”。
4chan最活跃的主论坛板块的免责声明写道:“这里的所有故事与信息均为虚构与谎言,只有傻瓜才会把它们当真。”正因如此,那些认真对待马斯克“纳粹敬礼否认”的记者和评论员,完全忽视了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对于马斯克的极右翼粉丝而言,他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种“故意挑衅却全身而退”的行为方式。
马斯克挑战了他所称的“觉醒心智病毒”(即所谓的“政治正确文化”),用“幽默”作为掩饰,将严肃问题转化为混乱和荒谬,从而彻底搅乱关于纳粹符号正常化的公共讨论。
这就是“钓鱼”操作的核心目的。看似“只是玩玩”、“为搞笑而搞笑”,实则是极右翼分子用来逐步右移社会舆论可接受范围(Overton窗口,这个“窗口”定义了哪些政策被视为可接受、合理或主流,哪些则被视为极端或不可接受,政治活动家和媒体通过推动公众舆论,可以使某些原本被视为极端的观点逐渐成为政策制定的可能选项)的策略。
马斯克敬礼事件发生后,极右翼人士如Nick Fuentes(美国第一运动的发起人,积极利用YouTube、Tele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其政治主张,尽管因仇恨言论被多个主流平台封禁,但依旧在极右翼圈层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他强调传统主义、男性主导权、基督教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应成为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并否认多元文化和世俗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Andrew Tate(英国出生的社交媒体人物、前职业拳击手,以其极具争议的“男性自我提升”言论和极端厌女主义观点而广为人知,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起一个以“高价值男性”理念为核心的全球追随者网络,经常鼓吹男性应以金钱、控制力和性征服为成功标准,攻击女性主义,否认性别平等,并以一种冷嘲热讽、暴力美学的风格进行传播,2022年因人口贩运、强奸及有组织犯罪等指控在罗马尼亚被拘留,其案件仍在调查中)纷纷模仿,并使用与马斯克相似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这些人正是通过网络亚文化积累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资本。
但其实,并不是只有极右翼才在使用网络梗图来推动政治目的。很多人认为,4chan等亚文化空间的形成,本身就是对“政治梗图化”(memefication of politics)的回应。
在《杀光所有常人:从4chan与Tumblr到特朗普与另类右翼的网络文化战争》一书中,安吉拉·纳格尔(Angela Nagle)指出,这种网络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2008年美国大选。当时奥巴马的“希望”宣传海报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被视为政治梗图使用的转折点。
但奥巴马政府并未兑现其模糊、乌托邦式的承诺,这种信息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催生出一种以不信任为美德的网络文化。随后在4chan等论坛上,任何坚定支持某党或某理念的人都会成为讽刺与攻击的对象。这种氛围逐渐形成一种玩世不恭、虚无主义的世界观。
快进到2024年总统大选周期,类似动态再次重演。哈里斯的竞选,依旧模仿奥巴马的风格,用空洞的梗图代替具体政策,而非提出任何脚踏实地的内容、现实中的政策。
相较之下,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联盟则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一种充满敌意、讽刺、厌倦政治正确的文化。他们没有试图用希望或进步主义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立场,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公开表达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和“主流媒体”的蔑视。这种策略在边缘网络空间中尤其有效,因为它与那里的文化逻辑高度契合:做出挑衅行为,然后在被批评时以“只是个玩笑”或“你太认真了”来掩盖真正意图。
在这种环境下,马斯克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他并不只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富豪,而且是一个深谙网络文化、懂得如何利用其隐晦语言和符号来激发共鸣的操作者。他将4chan等平台上的“梗文化”带入主流政治舞台,不仅拉近了这些边缘群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距离,还重塑了权力本身的语言方式。
他这种将讽刺、否认、攻击和“搞笑”融合为一体的风格,使得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不能被认真对待的游戏。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当政治被“表情包化”、被娱乐化到极致时,那些拥有最多注意力的人就掌握了最大的权力——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有毒、多么危险。
正如网络评论家和研究者所指出的,“troll文化”已经不再是无害的捣蛋行为。它成为了一种推动意识形态、影响公众话语的强大工具。如今,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越来越接近这种逻辑:不是通过政策来争取选票,而是通过引发情绪、制造对立、操纵叙事来掌握话语权。
马斯克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推波助澜。他帮助将一种曾经被边缘化、被视为极端的文化模式正常化、中心化,并通过他巨大的影响力将其输送到美国政治的核心舞台。
当他最终从特朗普政府中退出时,他留给这个国家的遗产将不仅仅是一系列失败的政治项目或争议言论,而是一个更加犬儒、更加极化、更加习惯于将仇恨包裹在笑话和“自由表达”外衣下的政治文化。这个变化,或许比任何政策上的失败都要来得深远且危险。
去年Clare Malone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就名为《美国政治的梗图化》,探讨了美国政治在当代社交媒体环境下日益“梗图化”的现象,尤其聚焦于乔·拜登总统的身体状况如何在网络梗图中被反复放大并塑造公众印象。政治人物形象塑造权在逐步下移,从传统媒体机构,转向去中心化、算法驱动的社交网络环境。
文章以拜登多次摔倒的影像为例,说明这些原本可能属于偶发的、生活化的细节,如何在TikTok、Twitter等平台上迅速转化为具有高度传播力的视觉素材,进而生成一系列“老态”、“不稳”、“不适合连任”等负面刻板印象。这些梗图经由讽刺、戏谑甚至误导性的再剪辑与转发,形成一种“视觉政治”的新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政治人物的身体动作、穿着、乃至走路的方式,都可能成为判断其治理能力的象征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登在任内诸多政策数据(如股市表现、通胀控制)显示出一定成效,但民众对其年龄的担忧却始终难以消解,这种感知显然部分源于梗图所带来的“感性强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特朗普年纪相仿,亦常表现出语无伦次或情绪化的一面,但他所遭受的“衰老叙事”远不如拜登那般强烈。这种非对称现象提示我们:在梗图文化中,“可被模仿”或“可被剪辑性”成为决定政治人物易受攻击程度的核心因素之一,而非实际政治表现。
文章还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不再通过传统新闻渠道获取信息,TikTok等短视频平台已成为他们主要的“政治入口”。新闻疲劳的蔓延,以及对“轻量级信息消费”的偏好,使得梗图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成为政治认知的基础单位。在这种媒介结构下,政治传播开始呈现出碎片化、情绪化、去语境化的特征,传统的论证逻辑让位于瞬时反应与视觉冲击力。
过去,拜登曾因其朴实幽默的个性在网络上获得一批“好感型”梗图支持,例如与奥巴马之间的“好基友”形象,以及其标志性的飞行员墨镜。然而,自2020年起,这种亲和力逐渐被保守派媒体主导的“迟钝老年人”叙事所取代,反映出梗图政治中立场倾向性与操控性的加强。
作者认为,这一趋势不仅挑战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模式,也对西方社会中政治认知的质量提出了严峻考验。
消失的女性自闭症患者
长久以来,自闭症都被认为是一种在男性中更为高发的神经障碍。相关网站、研究和期刊论文经常采用的数据是男性发病率为女性的四倍多,有时甚至会引用15:1这一数字。然而,《万古》杂志近日刊登的“自闭症中消失的女性”一文中介绍的新研究发现颠覆了这一传统认识,并且改变了我们对于自闭症的理解。
文章指出,在门诊中,男孩被转诊至自闭症评估的比例比女孩高出十倍,接受评估的男孩被确诊为自闭症的概率是接受评估的女孩的两倍多。多达80%的自闭症女性在被确诊之前都会得到社交焦虑、进食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等错误诊断。基于性别的社会化让很多自闭症女性尽力掩盖和内化自身的挣扎,使她们无法获得需要的帮助。
自闭症女性之所以被边缘化,部分原因是自闭症是男性的问题这个观念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研究人员致力于寻找“女性保护效应”,或将自闭症归咎于“极端男性化的大脑”。在关于自闭症患者大脑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有意将女性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男性”从来不是自闭症诊断中正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实现的预言。1943年,被称为“自闭症之父” 的奥地利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利奥·坎纳(Leo Kanner)描述了11个“早期婴儿自闭症”的案例,其中包括8个男孩,3个女孩,但随着“坎纳综合征”病例的积累,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男孩的发病率要高得多。1944年,奥地利医生汉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只关注了四个男孩,他更多地强调了这种病症的男性特征,称其为 “男性智力的极端变异”。20世纪80年代,自闭症的范围被扩大,诊断率大幅上升,但女性诊断率仍然很低,在一些报告中仅为6%-7%。达斯汀·霍夫曼在1988年的电影《雨人》中塑造了经典的自闭症患者形象——一个有着非凡技能和奇怪行为的男性,这种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自闭症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在诊断中采用的评估表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基于对已经确诊的个体的观察而提出的,这些个体通常是男性。医生在诊断时会询问家长孩子是否对诸如历史事实、日期、汽车品牌等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会注意孩子是否有缺乏眼神交流、不与他人接触的“孤独”行为模式,而不会仔细观察女孩玩洋娃娃、小马等看起来较为正常的兴趣以及她们表面正常的社会交往背后存在的刻板行为。
直到21世纪初,一批迟获确诊的自闭症女性才终于用她们有力的证词让公众意识到了自闭症故事中存在的空白。例如,劳拉·詹姆斯(Laura James)的《怪女孩出局:一个神经典型者世界中的自闭症女性》(Odd Girl Out: An Autistic Woman in a Neurotypical World,2017)和珍妮佛·库克(Jennifer Cook)的《穿高跟鞋的自闭症:谱系女性未被讲述的故事》(Autism in Heels: The Untold Story of a Female Life on the Spectrum,2018)揭示了她们作为局外人在令人困惑、高度社会化的世界中的长期挣扎。这些声音带来了改变,自闭症研究领域开始为性别差异提供框架,科学家开始主动招募女性参与研究,而不再回避她们或将她们的数据视为“噪音”剔除出去。
女性被纳入自闭症研究揭示了过往对于自闭症本质的认识存在错误,过去刻意回避社交和选择性自我孤立被认为是其本质特点。但对谱系中的女性进行仔细研究后,研究者发现她们身上存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特点:她们极力追求与他人的社交接触,执着地试图融入其中,获得归属感。为此,她们会密切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或手势,模仿其说话风格,甚至通过倾听他人的言语交流并私下反复排练来生成脚本。她们可能会创造出很多不同的身份和面具以隐藏自身,她们中有些人显得非常安静羞怯,有的则像在进行表演的假面舞者一般给人留下外向的印象。然而,这些伪装并没能帮助她们过上社交丰富的幸福生活,而是与高度的抑郁、焦虑、自杀意向和自残相关。
现在,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开始尝试识别这种伪装行为,去发现可能存在于外部表现和内心挣扎之间的脱节,甚至打破传统的自闭症评估方式,开始询问被评估者是否面临社交困境以及如何应对。自闭症神经科学也做出了调整,在“仅限男性”的研究时代,该学科关注的是负责支持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活动的大脑结构网络(即所谓“社交脑”)的异常低水平活动,而自闭症女性的“社交脑”的表现恰恰是过于活跃。也就是说,她们有着强烈的社交欲望,但和对于自闭症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的是,她们缺乏进行成功的社交互动的技能,因此她们发展出了精心设计的伪装模式,这最终导致她们受到伤害,并且更容易被忽视。“变色龙型”自闭症的发现,进一步拓宽了人们对于自闭症的认识。对于迟获确诊的自闭症女性而言,最终得到确诊为她们的生活和自我形象带来的巨大的积极影响,因为她们的首要人生动力就是寻找归属感,而尽管自闭症目前的定义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这毕竟是一个真实可识别的群体。
这一发现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在自闭症研究的各个方面正式纳入和理解“活生生的经验”的重要性。自闭症社区开始领导这项新增的参与性研究以探索该群体的非典型行为,自闭症患者作为合作伙伴被纳入从研究设计和招募、到研究解读和讨论各个环节。对于其他非典型行为领域而言,融入来自患者的独特专业知识同样能够带来好处。
对消失的自闭症女性的重新发现也为性别社会化及其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等更为广泛的问题带来了启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驱使大量自闭症患者(多数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自我伪装、以至于将归属感置于心理健康之上的力量,究竟是一种基因和激素决定的生物脚本,还是一种文化决定的社会训练机制,抑或两者皆有?
一则最近几年才被广泛认可的颇具讽刺性的历史事实是,自闭症的最早发现者并不是坎纳或阿斯伯格,而是一位名叫格鲁妮娅·苏哈列娃(Grunya Sukhareva)的苏联儿童精神病学家,她在1920年代率先发表了详细描述儿童自闭症的临床描述,并且对自闭症男孩和自闭症女孩进行了清晰的比较。《欧洲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期刊2021年发表、2023年刊登了一篇关于苏哈列娃的论文(“Pioneering, prodigious and perspicacious: Grunya Efimovna Sukhareva’s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conceptualising autism and schizophrenia”),对她的职业生涯、她对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概念形成的贡献以及坎纳和阿斯伯格没有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到她的可能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
据该论文介绍,苏哈列娃于1891年11月11日出生在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基辅,1915年毕业于基辅医学院,在该机构的流行病部门工作了两年后,1917年至1921年,她是基辅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医生。1921年,苏哈列娃在其导师米哈伊尔·古列维奇(Mikhail Osipovich Gurevich)领导的莫斯科儿童精神与神经部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创办了一所学校,她称之为“医院学校”,她对这所学校中的儿童的观察后来转化成了学术期刊论文。1928年到1933年间,苏哈列娃任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教授。1933 年至 1935 年,她担任哈尔科夫精神与神经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1935年,苏哈列娃成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在中央研究生医学教育学院成立了儿童精神病学系,担任系主任直至1965年。苏哈列娃被认为是俄罗斯儿童精神病学的奠基人,直到今天,苏哈列娃的著作仍然是俄罗斯儿童精神病学的主要教材。
苏哈列娃的“医院学校”开设了木工、艺术和体操课程,孩子们还有机会演奏乐器,学校还致力于向学生传授运动和社交技能,教师和医生密切合作,针对每个孩子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在坎纳和阿斯伯格发表其研究前近二十年的1925年,苏哈列娃在一本名为《教育学及儿童精神与神经学问题》的俄文杂志发表了对在这所“学校”中生活了两年左右的6名2岁到14岁的男孩的临床描述,他们表现出的症状就是今天所说的自闭症,这篇文章的德语版本于1926年发表在德文期刊《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月刊》(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上,题为“童年时期的分裂性精神病态”(Die schizoiden Psychopathien im Kindesalter)。这篇文章充满了同情的语调,在几乎所有案例中都强调了他们的天赋和才智,在倾向于关注他们在进入机构后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准确细致地描述了他们的非常规行为及其面临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哈列娃在对其中两个案例的描述中采用了“自闭的(autistic)”或表现出“自闭反应(autistic reactions)”的说法,在总结部分有一个章节的标题为“一种自闭的态度”(An autistic attitude)。她描述的儿童具有现代临床医生一眼就能认出的 “自闭症 ”特征,例如自动化倾向、缺乏心理灵活性和对新事物的适应性、情感的平淡和表面化、重复和不寻常的行为倾向以及对噪音的异常敏感等。
1927年,同样是在德文期刊《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月刊》上,苏哈列娃发表了1926年文章的第二部分,题为“分裂型精神病态在女童中的不同特点”(Die Besonderheiten der schizoiden Psychopathien bei den Mädchen),文中描述了五个表现出自闭症症状的女孩。在这篇文章中,苏哈列娃提到了病例存在“明显的系统化倾向”(与现代自闭症概念中的系统化相一致),且在对所有案例的诊断中都写到可以排除精神分裂症,并且认为外源性解释的可能性较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哈列娃对自闭症症状在男孩和女孩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指出两性在主要特征上的临床表现存在“重叠”,但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严重的情感障碍,她将这种差异归因为女性心理中更强烈和易变的情感。苏哈列娃对女性自闭症的关注比英语世界早了近一个世纪。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看来,坎纳和阿斯伯格都有可能读到过苏哈列娃的文章,但选择在自己的“开创性”论文中不提及她的重要贡献。坎纳在其1949年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苏哈列娃1932年的论文,但这不足以证明其1943年的文章受到了苏哈列娃1926年文章的影响。而阿斯伯格在这方面受到了更多诟病,有学者指出他在1944年的论文中描述的案例与苏哈列娃1926年的文章中的案例高度相似,也有学者认为阿斯伯格是因为与纳粹的关系而被禁止引用犹太学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