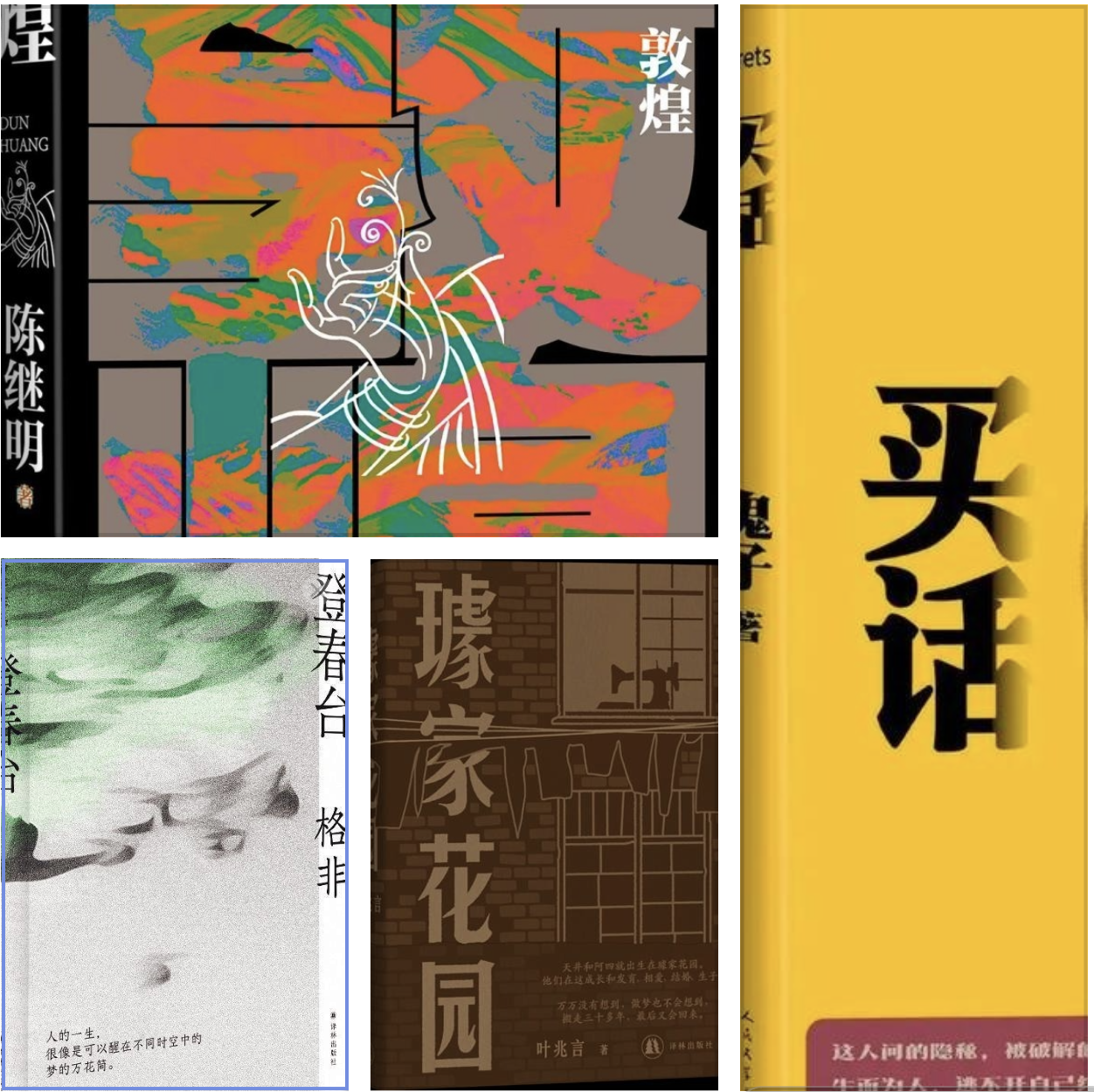黑料网-今日黑料:糖心饼干姐姐-自愿的强制关系:拉·波埃西的矛盾公式
【编者按】
当理想自我取代了权威,对每个人提出要求:你必须变得更好,成为你的理想。这对自我和社会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自愿服从于“自恋的痛苦”?我们又为什么要同意现状?
《自恋与服从》一书聚焦自恋,从经济、社会、道德等维度介绍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自恋”逐渐取代权威、信仰成为我们服从对象的过程,结合不同时期思想家如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福柯、阿尔都塞等人的论证,分析当前的过度竞争、量化管理、自我规训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看到自我陶醉的“我就是我”的矛盾之处。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1546年或1548年,法国作家拉·波埃西撰写了《论自愿为奴》(“Abhandlung über die freiwillige Knechtschaft”)一文。他创造了一个被广为引用的矛盾公式,将自愿性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自愿的强制关系。
拉·波埃西问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所有村庄、城市和民众,会忍受唯一的暴君呢?他的回答是:统治者的权力不会多于其被赋予的权力。暴君也一样。他只拥有应得的权力。他只在人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对他们造成伤害。因此,统治的秘密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被压迫者自愿接受统治者的压迫。这就是拉·波埃西给同时代人讲授的矛盾课程。他向他们呼喊:是你们让暴君变得强大!他的权力在于你们的自愿性!
拉·波埃西认为,要想获得自由,人们只需停止服从。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成为奴仆还是自由人。但人们同意自己的不幸,甚至追求这种不幸。
拉·波埃西说道:“这真是一种非常奇怪却又如此普通的现象。”
然而,为什么人们会服从呢(无论这对他们是否有利)?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这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还会服从呢?
拉·波埃西对这种矛盾现象做了如下解释:最初,对民众的征服可能是强制性的。但一旦被征服,民众就会“完全遗忘自己的自由”并自愿服从(freiwillige Unterwerfung)。但这种遗忘因何而起?强制性又是如何变成自愿性的呢?拉·波埃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通过欺骗和诱惑。换句话说,狡猾的暴君们巧妙地利用了强有力的手段:妓院和赌馆,公共娱乐和消遣,分发肉食等庆祝活动。“由此,他们欺骗了以肚腹为主人的底层民众。”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交易——但却是一场糟糕的交易,因为代价是自由。
其次,通过一切能助长轻信的事物来巩固统治。尤其是通过权力的饰品——浮华、谎言和宗教。也就是通过一切能蒙蔽人们的东西。
最后,通过习惯和教育来增强自愿性——它们会扭曲人们“生而自由”的本性。因此,自愿性不过是对人们追求自由这一自然倾向的扭曲。教育和习惯会埋没并破坏这种本性,这样一来,人们只能满足于自由的替代品,即自愿性。这一替代品通过习惯和教育变成了必然,违背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未经败坏的本性”。由此,自愿性替代了真正的自由,成为人们的第二本性。
拉·波埃西认为,服从的执念会深深地扎根,(自我)奴役已经成为第二本性。尽管如此,拉·波埃西仍然将他的文本作为一种呼吁、宣言和号召:“下定决心不再服从,你们就会获得自由。”只要人们不再同意成为奴仆,人们就能得到解放。就像第二本性可以轻易摆脱一样。拉·波埃西向同时代人发出的呼吁基于两点:一方面,他认为奴役是一种外在关系——尤其是它建立在强制和欺骗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他的文本中,自愿性的存在令人惊讶——它是缺席的。对一篇探讨自愿性的文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也许,自愿性之所以在文本中缺席,是因为它是一种缺失:缺失真正的、纯粹的、自然的自由。在他看来,自愿性只是被扭曲、被败坏的本性。
拉·波埃西的矛盾是一种既持续又可变的现象。它是持续的,因为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自愿的强制关系中。然而,它也是可变的,因为自愿服从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自愿服从仍然存在,但服从的形式和服从的内容不断变化。因此,它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强度、不同的实现方式和不同的理论化。如今,不再是自愿奴役,而是自愿服从。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服从者并不是主人的奴仆——他更多的是服从于关系并融入其中。与奴役不同,这样的服从并不将自己视为奴仆,它更像是一种同意——同意现有状况,接受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乔装打扮的强制关系中,自愿性似乎走向了其对立面:一种被视为授权(Ermächtigung)的服从。这种自愿服从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因为这是在支持、维护、延续现有秩序和现有关系时最深远、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既符合个人利益,又违背个人利益。
如果自愿服从既持续又可变,那么问题就来了:自愿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从何而来呢?
因此,我们要探索拉·波埃西所缺失的那种自愿性。在他那里,自愿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对他来说,自愿性只是走向自由这一“本性”的衰落形式。文明的扭曲埋没了自由冲动这一自然状态。
但这种探索不是考古式的,不是在文明的废墟中进行挖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只会证明拉·波埃西的想法。这种探索更多的是一种迂回——不是将社会理解为一种扭曲,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可能性,甚至是自愿性萌发的一种条件。
拉·波埃西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概念——自愿服从的矛盾公式。但他没有留下一个有效的定义。他的想法是,面对暴君的,是一个拥有决策能力的主体。无论这个主体的自愿服从是因为已经成为习惯的强制、欺骗还是诱惑,拉·波埃西的解释都是不够的。因为在以上这些情况中仍然存在一种外在关系。然而,自愿服从所需要或所依赖的,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内在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应该如何想象这样的关系?它从何而来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从16世纪的法国转向17世纪的荷兰。在那里,哲学家斯宾诺莎提供了关于自愿服从的另一种表述:人们会“为他们的奴役而战,就像为他们的救赎而战一样”。
他们不仅将奴役和救赎混为一谈,甚至还为此而战。为什么呢?
乍一看,人们会说:奴役意味着强制,救赎则意味着人们的期望和追求。人们是自愿的。但斯宾诺莎指出,国家的统治不仅限于强制服从。它还包括一切让人们自愿服从的手段。关键在于,这对斯宾诺莎来说并无区别。服从君主的命令,无论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对利益的期望还是对上帝或对祖国的爱,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臣民,不在于服从的原因,而在于服从本身”。
行为的自愿性本身并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奴役而是为了救赎。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愿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根据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行事。因此,自愿性并不能改变服从这一事实。在斯宾诺莎看来,关键在于,服从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自愿性不仅意味着服从命令,还意味着“全心全意”地这样做。因此,人们必须更进一步:自愿性并不会削弱服从这一事实,它反而增强了这一事实。斯宾诺莎由此得出结论,最伟大的统治来自“那些统治臣民心灵的人”。
不过,统治人心意味着引导冲动——引导爱、恨、蔑视等情感。例如,引导我们为自己的奴役而战,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救赎。然而,这些情感本质上是以君主为导向的。
在这里,我们理解了斯宾诺莎所说的“君主政体的最后秘密”:臣民混淆了救赎与奴役。他们不仅混淆了服从与自愿,还混淆了君主与上帝。
继内在关系之后,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关于自愿服从的关键词。在斯宾诺莎看来,这种服从的原型就是宗教,尤其是对一神论上帝的信仰。这个看不见的上帝被抽象地理解为纯粹的必然性,无法打动人心。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具象,也就是被赋予人们可以把握的形式时,例如,具象化为国王、摄政者、立法者,“仁慈、公正”——换句话说,具有人类特征。简而言之,上帝只有在被理解为人类,尤其是理想化的人类时才能打动人心。只有这种人格化、人性化的权威形象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只有白胡子老人的形象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增强服从的意识:全心全意的服从,不被察觉的服从。因为这种人类形象创造了自愿性的核心因素:与权威的“个人关系”(persönliches Verhältnis)。只有在个性化的上帝面前,人们才拥有爱的个人关系。只有这样的上帝才爱我,也只有这样的上帝才爱“我”。正如斯宾诺莎所说,这意味着,只有他爱我“先于其他一切”。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看见我,他在意我。而这种被在意性正是自愿服从和全心全意追随的驱动力,远远超出所有纯粹外在的、欺骗或诱惑的形象。

《自恋与服从》,[奥]伊索尔德·沙里姆著,桂书杰、包向飞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月。